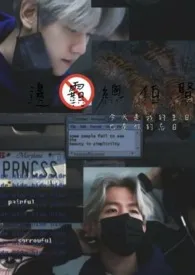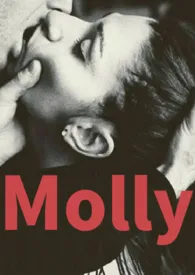搬到东院以前,蒋婶很少到我家串门,毕竟母亲和村妇们没什么共同语言。
当然,这并不是说母亲不好相处,事实上恰恰相反,她在村民中挺有威望和人缘。
一个表现就是,村里请长途车托运的物件,偶尔会就近放在学校传达室,由母亲代捎回来。
这些物件多数情况下是衣服,有时则是土特产、书本和化妆品,甚至也不乏证件、病例单等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记得九九年国庆节后不久——其时长者的蛤音犹在耳畔,母亲从学校带回一个大包裹。
据说是几个村妇托人在平阳买的什么内衣。
那两天秋雨绵绵,不时有人到家里来取衣服。
条件允许的话,她们还要亲自试一番才会心满意足。
有个晚上我和母亲在堂屋看电视,蒋婶伙同另一名村妇走了进来。
一阵寒暄后,她们便拎出衣服,在灯光下仔细揣摩起来。
老实说,妇女们在电视机前喋喋不休又锱铢必较的样子实在令人厌恶。
于是我索性躺沙发上,蒙头裹了条毯子。
眼前一抹黑,听觉却越发敏锐。
细碎的脚步声,窸窣的衣服摩擦声,咳嗽声,说话声,笑声,我甚至能想象口水从她们嘴里喷射而出,在灯光下绚丽地绽放开来。
这让我越发气闷,只好翻身侧头露了条缝。
不想堂屋正中的布帘没拉严实(其实从没拉严实过,没有必要),堪堪垂在耳边。
如你所料,透过两指宽的缝隙,一个肥硕的肉屁股映入我的眼帘。
它被一条大红棉布裤衩包裹着,浸泡在颤巍巍的灯光下,各种纹路、沟壑和光影历历在目。
虽谈不上多美,却是个货真价实的女人屁股。
我感到心脏快速收缩一下,就扭过了脸。
母亲和另一名村妇在东侧沙发上聊天,吴京因兽欲所困要跟焦恩俊拼命,那么,布帘那头无疑是老赵家媳妇了。
犹豫片刻,我还是小心翼翼地凑了过去。
这次看到了正面。
浑圆的大白腿,饱满的大腿根,微颤着的腰腹,扣子一样的肚脐,厚重的大红棉布胸罩和正乳豆腐般溢出的奶子,以及,一张惊讶而呆滞的脸。
蒋婶的眼本来就大,那晚瞪得像汤圆。
咣当一声,我脑子里给扔了个二踢脚,一片空白,甚至忘了及时撤出险境。
或许有那么一秒,俩汤圆迅速消失。
然后她麻利地提上裤子,冲客厅说了声“有点紧”,就转身去穿上衣。
我估计是的。
因为那时我已仰面躺好,正在妇女们的唧喳声中大汗淋漓。
蒋婶很快就回到客厅,在电视机前转了好几圈。
一片赞叹声中,她突然面向我:“林林,你看咋样?”
众所周知我没意见——除了语气词,我很难再说出其他什么话了。
蒋婶再进去时,我自然没敢动。
但不多时,耳畔传来椅子的蹭地声,身旁的布帘也不易觉察地掀起一袭波浪。
几乎下意识地,我侧过脸去。
出乎意料,横在眼前的是一条光洁圆润的大腿。
它光脚支在椅面上,于轻轻抖动中将炙热的阴部送了过来。
是的,几根黑毛打棉布侧边悄悄探出头,而我,几乎能嗅到那种温热的酸腥味。
至于蒋婶的表情,我没了印象。
或许她瞟了我一眼,或许她整个脑袋尚滞留于褪去一半的上衣中,又或许——我压根就没勇气抬起头来。
这之后再见到蒋婶,无论在家中、胡同里还是大街上,她都跟以往一模一样,以至于我不得不怀疑那晚是否是卧在沙发上做的一个梦。
但毫无疑问,有些东西被点燃了。
九八年那个秋夜后,待我从惶恐中缓过神来,立马被另一个问题所困扰。
我担心自己不长个儿了。
以前家里养狗时,父亲为防止伢狗四处勾搭,都会将其去势。
问原因,答曰“一瞎搞就不长了”。
这几乎构成我青春期最大的困惑,并在忐忑不安中促使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戒除了手淫。
然而当漫长的暑假来临时,我发现不少衣服都在变小,于是困惑和禁忌不攻自破。
其结果就是变本加厉。
那个夏天我疯狂地长痘,疯狂地手淫。
我在物理练习册背面绘上淫乱不堪的云雨七十二式。
我试着偷偷拨打成人声讯台。
我也搞不清自己用掉了多少卫生纸。
愚蠢的是,那些纸我没能及时丢掉,而是全部存在一个安踏包装袋内。
当然,此举并无特殊含义,归根结底是一个懒字。
有次打外面回来,母亲劈头就问:“擤鼻涕用那么多卫生纸啊?”
我“啊”了一声,她便不再多说。
直到吃完饭,我打楼上转一圈,看到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卧室时,才猛然意识到母亲在问什么。
这令我恼羞成怒。
等冲进堂屋,看着端坐在沙发上的一家子,我又发现自己无话可说。
于是母亲就建议我多运动。
我说我篮球打得还少吗。
她又让我练字。
我不置可否。
她说那就多看本书啊。
这时我猪肝色的脸已恢复如常,我问武侠可否。
她说:“也行,虽然不符合理想要求,但也凑合。”
事实上哪怕读古龙,当看到“充满弹性的大腿”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硬起来。
我觉得自己完蛋了。
有时候走在大街上,我会幻想和迎面而来的各种女人性交。
高矮胖瘦,我来者不拒,把她们肏得哭爹喊娘。
而一旦回到家里,便只剩下母亲。
伴着她的曼妙身姿,那个夜晚会时不时地溜出脑海,令我惊慌失措。
毫不夸张地说,一些红彤彤的傍晚,当我站在门廊下,母亲打一旁擦肩而过时,某种气流就会无可救药地从我体内升腾而起。
但当她扭过脸来和我说话,我又立马会羞愧万分。
于我而言,这已成为九九年夏天继骄阳、暴雨和汗水之外的第四个常态。
事实上,不光我,所有的呆逼都或豪放或羞涩地表示自己需要搞一搞了。
我们又没像小公狗那样被阉掉,为什么不能尽兴地搞一搞呢?
站在村西桥头,看着阳光下越发黝黑的鸡巴,我突然意识到:这或许是适合裸泳的最后一个夏天了。
然而就在这个暑假结束之前,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那会儿为了缓解经济压力,整个假期母亲都在某培训机构代课,辅导些高考作文什么的。
他们的传单和讲义我都瞄过,和全天下的同类一样,无时不刻在吹嘘自己多牛逼、多独特以及多有先见之明。
所谓先见之明,即在以往的高考历史中曾风骚地押中过多少多少题。
我问母亲这都是真的吗。
她先是呸一声,后又敲敲我的头:“人嘴两张皮,看你咋说了呗。”
显而易见,母亲只是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绝不是什么高考押题专家。
但条件非常之优厚。
每天只需两课时,薪水嘛,相当于以往五分之一的月工资。
那一阵父亲也不含糊,正撅屁股在工地上搬砖。
一段艰苦卓绝的适应期后,他老已游刃有余。
也许正是生活过于紧绷,父母不时会拌两句嘴,在还债问题上甚至一度吵得不可开交。
我清楚地记得,有次父亲为表达自己的愤怒,一屁股下去把一条塑料板凳坐得粉碎。
当时一家人正在楼顶吃饭,起初闷热,没什么风——真要有,也是鱼缸冒泡。
后来就起了风,伴着香椿和梧桐的摇曳,塑料碎片欢快地四处翻滚。
而父亲坐在地上,死命嚼着黄瓜,任奶奶说破嘴也不起来。
母亲比他还要沉默,她有种嚼黄瓜都不出声的技巧。
那个永生难忘的早晨便是这个奇异傍晚的延续。
工地上一般六点半出工(户外作业会更早),父亲起码六点钟就要吃饭。
其结果是每天我睡眼惺忪地打楼上下来,都要孤零零地面对一锅剩饭。
“老妈子”母亲不消说,奶奶也是个酷爱早起的主儿——自打爷爷去世,她便皈依了晨练教,机缘巧合的话至今你能在冒着露水的林子里听到她嘹亮的嚎叫。
总之用母亲的话说,我“就是太懒才落了个孤家寡人”。
早饭多数情况下是面条,这当然也是为了照顾父亲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对此我不敢有意见,但山珍海味也搁不住天天吃啊。
母亲却不以为然,她认为一日有三餐,营养够均衡了,以及“真不满意,想吃啥可以自己做”。
我自然没有自给自足的能耐,除了祈祷雨天,也只能指望奶奶了——她老要碰巧在家,兴许会帮我熬个粥、煎个蛋、拍根黄瓜什么的。
但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于是只身一条三角裤衩成了我出门前的标配。
我觉得这样十分符合气候条件,又不会妨碍行动自由,情绪所至时还能酣畅淋漓地大打飞机。
那天便是如此。
在大太阳炙烤下,我顶着帐篷迷迷瞪瞪地下了楼,打厕所出来又一路走走停停,怡然自得地翻了好半会儿包皮。
待我在凉亭里坐下,踌躇满志地准备搞一搞时,厨房里突然传来母亲的声音。
她说:“快洗洗吃饭,一天磨磨蹭蹭!”
如你所料,我险些当场瘫掉,鸡皮疙瘩在汗流浃背中掉了一地。
穿好衣服再打楼上下来,我往厨房偷瞟了一眼,竹门帘的缝隙里隐隐溢出个朦胧背影。
我想说点什么,却苦于口干舌燥,愣是捏不出半个词句。
直到刷牙时,在院子里兜了两圈后,我猛一抬头,正好撞见母亲透过纱窗的眼眸。
她说:“看你能有多懒。”
声音平缓,语调轻逸。
于是我喷着白沫口齿不清地问:“咋没上课?”
母亲没了影,锅盖像是掀了起来。
好半会儿她说:“快刷你的牙,嘴里都憋些啥啊。”
那天母亲在烙饼。
刚撩起门帘,油香就窜了出来。
她面向灶台,马尾高扬,却没瞅我一眼。
我只好吸吸鼻子,问她咋没去上课。
母亲把油饼翻个面,对我的问题置若罔闻。
我只能又重复了一遍,完了还叫了声妈。
“调课了呗,”母亲总算扭过脸来,挥挥铲子,努努嘴,“快吃饭,今儿个可不是面条。”
于是我又看了她一眼,就去盛饭。
母亲穿了条乳白色的真丝睡裙,略清凉,腰部扭转间曲线便涌动而出——连宽大的裙摆也无力遮掩。
此睡裙是陈老师从上海捎回的特价货,上面吊带,下面刚刚盖住大腿,在那年头还挺摩登。
至少省卫视就播过类似的购物广告,我没少偷看。
那个夏天在楼顶纳凉时母亲都这身打扮,但这大白天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当然,怪我懒,于清晨的我而言母亲不免只是院子里的几声鸟鸣。
其实刚一进门,那右侧臀瓣上浮起的内裤边痕就让我心里一跳。
我觉得它颜色太亮,又过于光滑,以至于有些晕眼。
锅里是鸡蛋疙瘩汤。
我问母亲吃饭没。
她切了一声。
于是我就盛了两碗,并且说:“别跟他一般见识。”
她扭过脸来,说:“啥?”
我吸吸鼻子,又重复了一遍,与此同时勺柄碰得锅沿叮叮作响。
她说:“别跟谁一般见识?”
“我爸——呗。”
迟疑了下,我觉得加个“呗”很有必要。
母亲没搭茬,而是瞅了我两眼,然后起了张油饼出来。
走向案板时,她说:“腌韭菜还有,想吃黄瓜拍根黄瓜。”
老实说,母亲的反应让我自觉很突兀,不免有些害臊。
把汤端到堂屋后,我呆了好半会儿才又回到厨房。
这时母亲已拍好黄瓜——事实上我也正是循声而来。
“仨饼够不?”她挪挪铁凹上的油饼,微侧过脸,“柜子里还有俩西红柿,自个儿洗去。”
于是我就途经母亲去取西红柿。
正是此时,她突然揽住了我的脖子。
柔软、馨香、温热以及明亮,一股脑涌了过来——母亲在我额头上轻抵两下,语调轻快:“还是儿子好,好歹知道向着你妈。”
我不知作何反应,心里怦怦直跳,腰上却像别了根棍子。
而她皓腕里,铲子轻扬,油光光地印着我的脸。
我清楚地记得,那扭曲的鼻孔和通红的痘痘被不负责任地放大,显得分外狰狞而愚蠢。
半晌我才挤出了仨字。
我说:“那当然。”
脑袋热烘烘实在是种糟糕的感觉,就像有人凿开你的脑壳往里拉了泡屎。
随着屎的渗透,你整个人不由轻飘飘起来。
我蹲地上拿西红柿时就是这么个状态。
晕乎乎的空气中,光洁的小腿近在脸侧,白得令人目眩。
我甚至想到,只要头再低点,贴着小腿抬起眼皮,就能一路向上看到母亲的身体。
这让我心里一阵麻痒,抓起西红柿时手都有点发软。
母亲却在喋喋不休,说我懒,说什么正长身体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
她甚至恐吓我还想不想长个儿了。
我只是偶尔哼一声,自然没放在心上。
事实上我整个人都涣散无力,再也承受不住任何重量,哪怕是只言片语。
而当这些或轻柔或苛责的话语在逼仄的厨房里飘荡而过时,圆润的臀瓣也不时蜻蜓点水般于宽大的裙筒中浮现出来。
记得洗完西红柿,我问母亲要不要搁点蒜。
她啧一声,指指我的脸:“瞅你脸多光呢。”
说这话时,眼前的胴体轻盈地跳了跳。
于是一些柔软而突出的部位也跟着跳了跳,继而细腰和小腹便在睡裙的褶皱间原形毕露。
我赶紧撇过脸。
母亲却开始科普祛痘心得,叮嘱我别乱抠乱摸,特别是别用她的洗面奶。
欢快的语调中,她的腰肢都不易觉察地摇曳起来。
搞不好为什么,如彼时窗外的绚烂世界,我心里猛然一片亮堂。
于是在走向案板的途中,我的右手背挨着母亲屁股蹭了一把。
这令我大吃一惊,以至于当那份丰隆和光滑在心头响起时,我近乎赌气地说:“不用就不用!”
是的,作为一名拙劣的演员,僵硬和颤抖使我像个公然炸裂的气球。
然而母亲似乎没有觉察,她说:“你看你,这不都为你好?化妆品能乱用?嗯?妈的衣裳你能穿?”
大致就是这么个意思吧,我没敢回头看,但能轻松地想象她的表情和动作,包括游移于唇鼻间的那股子戏虐。
事情当然没有结束。
切西红柿时,母亲说让她来,被我斩钉截铁地拒绝。
我感到脸涨得厉害,某种莫名的不安驱使我责无旁贷地落刀。
难得的从容不迫。
我近乎痴迷地把眼前不知该归类于蔬菜还是水果的玩意儿等分成无数多的小份。
母亲好像始终站在一旁,也许哟了一声,也许什么都没说。
只记得清晨的阳光打南侧窗棂攀进来,迈过暗淡发青的白灰墙,在我身前的柳木擦子上踩出尖尖一脚。
而我呵着腰,伴着噔噔脆响,任由坚硬的老二抵在案板下的抽屉楞上。
有那么一刹那,我甚至觉得可以把整张案板翘起来。
等西红柿切完,最后一张油饼也宣告出锅。
黄瓜自然由母亲来拌。
在她扇出的香风中,我侧过身子,隔着裤兜捏了捏尚在兀自充血的下体。
我能看到母亲翁动的丰唇,娇嫩多褶的腋窝,以及在颤动中不时浮凸而起的乳头轮廓。
她在说些什么呢?
我完全没了印象。
后来隔着母亲拿筷子时,我就顶在了肥硕的屁股上。
这种事毫无办法。
当熟悉而又陌生的绵软袭来时,我险些叫出声来。
母亲似乎颤抖了一下,她飞快地扭过头来——于是马尾在我脸上扫荡而过。
那扑面而来的馨香,那雪白的臂膀和修长的脖颈,无不令我头晕目眩。
别无选择,我抱住了她,与此同时粗暴地挺起胯部,仿佛真有一个洞等着我钻进去。
母亲肯定发出了声音,或许是个语气词。
但我把她抱得更紧了,我说妈,我甚至无师自通地攥住了两个乳房。
我能感到那柔软的弹性和温暖的乳头正从指缝间悄然溢出。
母亲又叫了一声。
这次我听清了——是“严林”。
然后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将我挣脱开来,并顺带着拂过我的脸颊。
啪地脆响,一轮骄阳打厨房里升腾而起。
我也记不清在厨房站了多久。
起初还能看到光洁的腿和玲珑的脚,后来就只剩下乌黑龟裂的水泥地面。
而汗水汹涌而下,不等砸到地上,便模糊了视线。
母亲先是进了洗澡间,后又回到卧室,不一会儿就“嗒嗒嗒”地出现在院子里。
开了大门后,她便推上自行车,径直走了出去,临行也没忘了关门。
整个过程中她没说一句话,没准看都没看我一眼。
于是我一个人喝了两碗汤,油饼和凉拌黄瓜却没碰——不要问,我也搞不懂为什么。
奶奶回来时还抱怨母亲没个度,连自己能吃多少也不知道。
完了她指着我的脸说:“这边儿的疙瘩痘咋肿了,那么红啊,可不敢乱搓!”
我无力地笑了笑,除此之外真不知该作何反应。
毕竟那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挨耳光,况且还来自母亲。
我觉得几乎顷刻间,所有的躁动不安都令人惊讶地迅速退散。
我伸伸触角,一切又平静如水。
当天吃午饭时母亲来了个电话。
刚接起我便知道是她——那均匀轻巧的呼吸一如既往,总让我想起新叶背面悄悄伸展的细密纹路。
谁也没说话。
我连声妈都没能叫出来。
奶奶好奇地问:“谁啊?”
母亲总算开口了,她说:“电话给你奶奶。”
于是我就把电话给奶奶。
她们说些什么我不清楚,倒是奶奶不时扫我几眼,评头论足的唔唔嗯嗯令人毛骨悚然。
放下电话,她老长叹口气,便不再言语。
我埋头扒饭,心头的鼓不由越发紧密急促。
直到一碗白米饭下肚,奶奶都没说一句话。
我实在忍无可忍,只好问:“咋了?”
“啥咋了?”
“我妈咋了?”
“你妈没咋,”奶奶又是一声长叹,“倒是你这疙瘩痘,我看还得找个老仙儿对方子,你妈非要买啥洗脸奶,瞎折腾一天。”
就是这样。
那天我扎在呆逼堆里打了一下午双升,之后又结伴捣了会儿台球,回来时天已擦黑。
趁一家人在楼上纳凉的功夫,我缩凉亭里,于蚊虫叮咬下吃完了饭。
飞快咀嚼的同时,我下意识地竖起耳朵,去捕捉母亲的动静。
然而一无所获。
等收拾好碗筷,打厨房出来,我却险些撞上母亲。
淡薄的星光下,她着一件碎花连衣裙,披散着的长发犹如晚风新发的嫩芽。
我想说点什么,却只是撇过了脸。
母亲也没说话,她摇着蒲扇,转身上了楼。
我在院子里杵了好一阵,最后还是进了堂屋。
那支可怜可俐就立在茶几上,我一直没动,直到有一天它自己卸下包装跑到了洗面台前。
母亲的不理不睬持续了好几天,连父亲都发现了异样。
他偷偷问我是不是招惹母亲了,我一时面红耳赤,屁都放不出一个。
于是一次午饭时,父亲宣布:“现在的小孩啊,喜欢搞点青春叛逆,叛逆个屁啊,要让我遇着,屎不给他们打出来!”
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我瞥了母亲一眼。
她头都没抬,只是面向父亲说:“吃个饭,你能文明点不?”
除了一声嘟囔,后者无言以对。
片刻后,在奶奶的不动声色中,母亲又转向我:“可别跟你爸学。”
这句话令我打了数天腹稿的长信宣告流产,也让我愈加坚信:父母与子女
通信是影视作品里才会出现的滑稽桥段,乃是一种艺术加工,或者确切点讲——一种不可理喻的华而不实。
毫不夸张地说,那个令人羞愧的早晨像座突然崛起的堤坝,把我体内跃跃欲试的潮水收拾得服服帖帖。
好长一段时间后,我才重拾手淫的乐趣。
至于蒋婶,我说不好,或许她只是恰巧处在那里吧。
就如同九七年夏天在平河滩上偷瓜,你选定一个,必会被另一个所吸引。
那不计其数的西瓜似河面上的波光粼粼,令人眼花缭乱。
而犹豫等于被俘,如果你真的口渴难耐,唯一的正确做法是就近抱住一个就跑。
九九年冬天后,蒋婶就经常在家里走动了。
她不打正门进来,而是走楼顶。
有好几次,我见她拾阶而下,毛衣里的奶子像不时飘荡于院子上空的嗓门般波涛汹涌。
多数情况下她会找奶奶闲聊。
当然,碰到父母在家也会扯几句。
比如那年母亲在卢氏给我做了套西服,她看了直夸前者有眼光,还说我瞧起来像个小大人了。
这算不算某种鼓励我也说不准,总之冬日惨淡的阳光驱使我在她丰满的身体上多扫了好几眼。
那个冬天多雪,2000年元旦前后积雪甚至一度有膝盖深。
于是人们就缩在煤炉桌旁烤火——那是一种类似于炕的存在,下面炉子上面桌子,至今北方农村靠它取暖。
有天晚饭后我趴桌子上看书,周遭是喋喋不休的众人。
他们的唾液绕过电视剧和瓜子后依旧充沛有力。
蒋婶就坐在我身侧。
可能是某个搞笑的剧情后,她的腿悄悄在我腿上碰了一下。
之后就是无数下。
这令我大吃一惊,却又无可避免地振奋起来。
作为回应,我忐忑不安地在那条丰满的大腿上捏了几把。
我甚至想长驱直入。
但她猛然攥住了我的手。
一番摩挲后,那个多肉的小手围成一个圆筒,圈住了我的中指。
是的,伴着耳畔粗重而压抑的呼吸,它轻轻地套弄起来。
我不知作何反应,只能僵硬地挺直了脊梁。
记得我看了母亲一眼,她正好撇过脸来,说:“少吃点瓜子啊你。”
然而某种令人作呕的东西正让我迅速勃起。
毫无疑问,那已是近乎赤裸的交配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