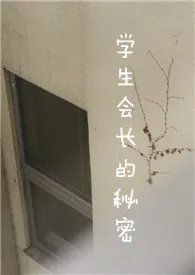秋日的清晨阳光柔魅,高飞的云雀欢唱之声不需清风也能捎来阵阵脆亮。
水雾像层薄薄的轻纱,旖旎而妩媚。
可一片片的叶子由青转黄,终究在干枯了之后落下,旋转着,跳跃着,带着无尽的遗憾无可奈何地投入大地的怀抱。
柔惜雪推开房门时,正面对落下了不少枯叶的院子。
她心中一跳,在忧伤的季节里,人总难以避免往日的思念与惆怅,即使淡漠如她也不例外。
——那股峭然的愁绪就像山溪一样时缓时急,在无尽的秋风里悄悄潜入人心,排不开,躲不去。
她双眸一黯,情不自禁地垂下头低吟经文,迈着沉重的步伐向佛堂走去。
脚步的沉重不仅是深深的自责与负罪感,也因功力全失,身躯慵懒无力,才使得院落里路虽平,步伐难安定。
天阴门里百余年传承连同着广厦屋舍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同门死的死,归顺的归顺,震撼世间百年的天阴门金字招牌如今片瓦无存,只留下几个幸存者苟且偷生,寄人篱下。
更可恨的是,两名仇人仍自逍遥,一人已是万乘之尊,另一人也大有可能成为万乘之尊。
支撑自己苦熬二十年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前途渺茫看不见任何希望,自己犹似个活死人,不是活死人还能如何?
佛魔双界分,人间劫纷纷;普法降甘霖,苦海现佛尊。
可笑心中一片礼佛赤诚,危难之时佛祖不曾显灵,甚至没有点滴护佑。
如果佛祖要给自己劫难无数,那同门又是何辜?
念珠上的名字就像用刻刀划在了心口里,鲜血涓涓难止。
柔惜雪面目表情地木然拿起念珠盘上手掌,燃香插好,盘坐在蒲团上低声诵起经文来。
佛祖不显灵,可一身罪业无从寄托,仍需歌颂着佛号寻求一点点心灵的慰籍。
否则不再威力无穷的身体早已不堪承受。
诵过了几篇经,柔惜雪睁开眼来。
目蕴雷电,几乎能直透人心,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模糊的视线,好一会儿才能聚集在一起看清。
人之寄情于虚无缥缈,大多源于无力与绝望,现今这个没用的身体,愿望再多再好又有什么希望呢?
柔惜雪又木然起身,唯因坐久了腰腿酸麻而微蹙了蹙眉头,步履蹒跚地一顿一顿挨至石桌。
时至今日,黯然已变得麻木,就像血行不畅的腿脚一样,没有什么神妙之方,只能等着慢慢恢复。
可悲的是,不久之后又将是一个循环。
蒲团前祈祝,石桌前稍事休息再发发呆,已是她的所有。
这座小院就是她全部的天地,仿佛藏在这里就能躲开讥嘲与鄙夷,以及生生世世都难以偿还消弭的罪业。
吱呀声响起,娇小的身影闪了进来。
小院不闭门,也时常有些人会来,比如前日的吴征与祝雅瞳。
覆灭的天阴门里,最为熟悉亲近的另三位幸存者都对她保有尊敬,但唯有这个娇小的身影才能让柔惜雪心中一暖。
对她的栽培,还有从前一番维护的苦心没有白费。
这个冷冰冰的弟子不知何时被剥去了身周的坚冰,越发活泼,越发可人,甚至有一股激人向上的力量。
而她现在终于明白自己为何强要将她许配给皇室,打心底全是出于对她的爱护。
更加庆幸的是,自己的一番好意终究没有称心如意,否则现在她要面对怎样的苦难。
天家无情,最安全的后路也是万丈深渊。
“师尊。”冷月玦背着个背囊,双掌在小腹前捧着一大迭直抵脖颈的书册,以下颌按稳了行来放在石桌上,拍了拍手道:“徒儿来晚了,师尊勿怪。”
“嗯。”即使心生暖意,柔惜雪依然淡淡地应道,徒儿的用心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然而一切都不会有什么不同。
自己没有开口,只是从前对她苛求太多,现下没了未来和希望,不如由得她去了。
“吴掌门来信说您答应了要一同重修典籍,徒儿刻意多拿了些空白书册来,等用完了再取。”冷月玦解开背囊,整理出狼毫香墨,砚台笔洗道。
“什么?”
“嗯?”师徒都是清净寡淡的性子,但互相之间颇为知心。
柔惜雪不明所以,冷月玦便醒悟过来道:“他诓我……”
少女红着脸,三分薄怒,三分嗔怪,另有四分羞悦,似在娇嗔情郎拿她玩笑取乐,却偏生没有半点怪罪。
那楚楚动人的俏脸纯真而明媚,正是发自心底的爱意才有的模样。
柔惜雪心中一动,竟生出些羡慕来。
她当然知道徒儿生就一副绝色之姿,可从前又哪曾见她这般模样,又何曾会去关注她一喜一怒的娇俏。
“师尊既没答应也无妨,徒儿来做就是。”冷月玦一边磨墨,一边自顾自地道:“他们昆仑派重修典籍之事进展甚速,咱们天阴门也不能差了。师尊您忙您的,空闲时若是无聊,帮着徒儿看一看是否有缺漏可好?”
“嗯?”柔惜雪张了张嘴,最终未发一言,只看着冷月玦摊开第一本未曾装订牢固的书册,翻过封面,在扉页里写下二句。
“昆仑也是一身的血海深仇,但和咱们天阴门相比还要好上些许。吴掌门不服输,不认命,门人士气也旺,连林师姑都打着精神。徒儿前段时日又旁事缠身挤不出功夫,咱们天阴门气势上可不能弱于昆仑派,现下开始追赶也不迟。师尊重伤初愈也不忙于一时,从前师尊照料徒儿多年,现下让徒儿来照料师尊,打点门派。”冷月玦细心地写下两句七字诗,举起来以嘴轻轻吹干摆在柔惜雪面前曼声吟道:“手握灵珠常奋笔,心开天籁亦吹箫。师尊您看吴掌门赠的这二句如何?”
一口一个吴掌门,叫的如口中含蜜,甜腻无比,与嘴角淡淡却掩不去的笑容相得益彰。
柔惜雪心中暗叹,爱徒已是全心扑在吴征身上,爱的铭心刻骨。
想来吴征待她也是极好,才能让冷月玦这般情深。
——除了疼爱之外,帮衬也是竭尽全力,冷月玦不灰心丧气反倒斗志昂扬,只怕吴征占了好大的功劳。
柔惜雪心下颇宽慰,比起自家从前的孤军奋战,爱徒有能人诚心诚意地帮衬,就是大大的幸事。
从前严苛的性子随着武功的消失,希望的泯灭似也消散,只要爱徒开心便好。
柔惜雪轻声道:“昆仑是道家,修行法门与咱们佛宗有别,这两句么……”
“吴掌门说,天下大道殊途同归,武功如此,修行也是如此。佛也好,道也好,不都是劝人向善么?”
柔惜雪不愿与爱徒争执,只道:“依上下两句的意思,这个[亦]字当用[不]字更妥些。以他的才智,不知是怎生想的。”
“师尊所言大有道理,此前我也这么想,到了这里我才忽然明白个中之意。”
冷月玦兴高采烈道:“若是这里用不字,两句的意思便是说自家修行,即使灵珠在握也不可忘了精益求精,修行更上一层楼。而这些均未必为外人所道,心有天籁之音何须鸣萧奏曲,悟得大道自当远离凡俗。可是我等均是俗人,在凡俗中为声名所累,恩仇所牵,现下这座府邸里的每一位都是如此。若是只做自家修行,岂不是逃避现实?这个不字改作了亦,含义便截然不同。昆仑派也好,天阴门也罢,岂有甘于沉沦者?师门恩重,徒儿就算哪一日悟得大道,必然引吭高歌,叫天下知晓,重振天阴门才对。”
冷月玦说完,院里一时没了人声,只余她兴奋地左右踱步时踩着落叶的沙沙声。
柔惜雪仍是木然着脸庞,许久才道:“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这一席话说下来,让柔惜雪觉得比爱徒一辈子说过的话都多。
而看她略有些兴奋地逡巡着,柔惜雪猜测是不是得到了什么保证,才会如此激动。
“是。只是徒儿先行应承了吴掌门保密,现下还不能说与师尊。”冷月玦大方地承认,歉然道。
“嗯。”柔惜雪随口应道,随手拿起了支笔,随意摊开一本书册自言自语道:“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写字了……”
提起的手臂颤巍巍的,手掌也远不及从前的稳定。
可笔锋一落在页面上留下墨迹,柔惜雪脑中便不自觉地涌过无数从前藏经阁中的典籍,妙语,再也停不下来,唰唰唰地写了下去……
……………………………………………………
即使在多雨湿润的江南,在草叶枯萎的原野里,萧瑟的秋风起时依旧刮得漫天尘土飞扬。
什么枯黄改变了世界的眼色,还是最浪漫的季节,再好的形容与赞赏都让尘土给吹得一干二净。
吴征实在不喜欢这个季节——久久没有一场雨,只消起了风,不需多时就能让桌面浮上一层灰土。
一个时辰不擦,摸上去便是又粗又脏。
何况是在旷野中的军营。
大风天气卷来的沙土能让人在呼吸间都吃上一嘴的灰。
吴征与身旁的营中兵丁们都不由自主地眯起了眼,重重朝地上吐了一口。
拉好了架势,目光还百忙之中朝操演的校场边一瞥。
军营里的血气旺盛,当然夹杂着豪爽男儿的体味。
一天操演下来,旷野中似乎都是汗臭。
向来优渥,又有过军中经历的吴征尚且有时难以忍受,何况娇滴滴的女子。
张圣杰的旨意一经宣读,倪妙筠便正式成了监军,与吴征同桌而食,出入结伴,近乎形影不离。
只是那日的调笑过后,吴征几回搭讪均换来白眼冷哼,任凭他舌灿莲花说尽了好话,除公事外再无半句闲谈。
几回碰壁之后吴征学的乖了,说什么好话?
说一回,便是提醒美人一次失言之举,便是让她再难堪一回。
时至今日,吴征依然心中好笑,望向倪妙筠时也不免打心眼里佩服。
大学士的女儿,偏生要来军营里受罪。
虽说她担负监军之职不需操演,照样也是诸多不便。
今日刮着大风,很快也让她的衣甲蒙上一层黄沙。
秋风又何解风情?
佳人的秀发与娇颜上同样是肉眼可见的灰土。
“咳咳……”韩铁衣清了清嗓子,点着校场运足了真气道:“今日和从前一样,兵器任选,三十人为一组焚香为记,闯过去用时少者为胜,最终胜者可免半日操演。至于这位胜者之外的么,呵呵,不好意思了,午后加练。”
这种大操演五日一回,吴征还是第一次参加。
校场上设置了重重障碍,事先以黑布蒙上,让人看不清其中的机关。
——战场之上,哪有什么预定的套路。
这迷宫一样的校场,不是亲身进入从外难以得知个中玄机。
吴征所处是最后一组,韩铁衣所宣称的抽签决定其实还是暗箱操作了一回,否则以吴征鹤立鸡群的功力,一上场便要断了其余人夺取头名的念想。
信香点燃插入了香炉,比赛便即开始。
三十人争先恐后地冲入[迷宫],便见密密麻麻交错的丝线如蛛网一般,显是设置好的机关。
丝线缝隙一指难容,绝不可能不触动便闪过去。
吴征气运丹田鼓足了目力,身形丝毫不停撞开丝线,但听砰砰砰暴雨般密集的弦音想起,周围土壁上无数竹箭射了出来。
竹箭无尖,若是任由打在身上也不好受,更难过的是顶端均裹了只粉包,打到身上便是令人难堪的记号。
三十人前后撞入,黑布蓬里的竹箭全数发射出来,从不同的角度四下乱飞,像极了战场上流矢处处,无迹可寻。
吴征躲不开丝线,但使开[听风观雨],竹箭的来龙去脉却尽在脑海。
他伸手一抄捉了根射向面门的箭枝在掌,挥舞着拨打箭雨。
优胜者仅能有一人,那些颇为自负的,或是自觉有望争先的,互相之间怎可能相安无事?
另有些纯属看吴征不顺眼,想着法儿找机会使绊子。
吴征挥手挡开迎面的两箭,一个纵跃横着身子低飞过去让身后袭来的箭枝落了空,这一下子还窜到了前排,在误中副车者的咒骂声中回身笑道:“要暗算我,那就跟得紧些。”他手足不停,一边轻易地拨开箭枝,一边连连点地,与众人越拉越远。
这一下使出了真功夫,众人便自觉与他差得太远。
这般举重若轻,无论内外功都已是上乘之选,加之此前见过他闯阵的本事,心中气馁也好,不爽也罢,都不免暗暗佩服。
穿过了箭雨,前方微弱的灯光里现出一个拐弯。
吴征刻意显摆武功立威,足下加劲侧着身转过,不防眼前忽现数百杆竹竿!
韩铁衣的布置极为巧妙,精准地卡住了视线的死角,不转弯看不见,一转弯已在眼前。
竹竿便是长枪的模样,数百杆列在一起,仿佛长枪如林。
吴征应变奇速,几在间不容发之际一点足尖,借着前冲之势飞跃枪林。
枪林之后,还有枪林,这一片后置的枪林尖端朝天,且不再是枪头上包着粉包,而是真正削得尖了,虽非金铁,扎上了也要挂彩。
两片枪林,除非肋生双翼否则不可能一跃而过,但对轻功高手而言不是问题。
吴征伸手抓住枪尖腰杆发力,两个翻身腾跃冲了过去。
这一下翩若飞鸟,校场上围观的军士们发出连连的彩声来。
到了军营之中,无论愿不愿都只能认命,否则做了逃兵不是闹着玩的事情。
军中最令人敬佩的就是强者,军士一层而言,对勇力的敬佩更甚于智计。
吴征飞纵腾跃,不仅迅捷无比远远拉下了后续的竞争者,且姿态潇洒,大有举重若轻之感,就更加叫人佩服。
连过箭雨枪林两关,前方道路分岔,进入后又是陷阱处处,檑木过后又是滚石,将战场上的一切模拟得十足十。
吴征避开檑木阵后跃入土坡,这一处是校场上唯一能看得清的所在,但见一人高的滚石连珠炮似地顺着山坡压了下来,无机巧可言,唯凭个人能耐与勇气。
吴征大喝一声,力贯双臂左右连挥,将一人高的滚石连连拍开。
此前也有外功高手硬闯此阵,但绝没有吴征的迅捷,凶猛,精准。
他一边大踏步地前进,一边拍击,巨石应声偏飞,足下稳稳当当地前进。
这一手功夫不仅显露了高明的内功,更显身子骨强劲有力,内外兼修已达极高的境界。
在场都是行家,更是引起震天价的叫好声。
上了坡顶,又是一堵三丈高墙,翻过高墙便是终点。
吴征刻意卖弄,足尖在这里一点,双掌那里一按,施展开昆仑轻功青云纵,像一抹青烟一样跃上高墙之顶。
回首四顾,只见离得最近着也不过到了檑木附近,燃起的青香也不过烧了一半多些。
一时之间,吴征也有些得意,自幼起的勤修苦练,辅以[道理诀]的神奇与完全符合他个人特质,终于也到了即将登临绝顶,可以俯瞰芸芸众生的这一步。
再有三五年的时光,自己还会怕谁?
普天之下的高手谁敢正眼看吴府?
韬光养晦的盛国会强大起来,吴府也会有应对天下高手的力量。
“霍永宁!你给老子等着!”吴征忽然面目狰狞地一咬牙,冷哼一声跃下高墙,虎着脸一屁股坐在韩铁衣与倪妙筠当中的位置上。
大获全胜,殊无喜意,主将心情不佳似发了怒,军士们自然有些心头惴惴不安,噤若寒蝉。
“恭喜恭喜。”韩铁衣低声道:“吴将军今日大发神威,要收服这干野性难驯的猴子也就差了一席话之功,不知吴将军准备好了没有?”
“好不容易想了些生气的事情板起脸!老子现在杀气这么重,被你一调侃你说多尴尬?”吴征嘴皮子微动,憋着怒容道:“前头你往死里折腾他们,一副要折腾出营啸的模样,还以为你有什么高招要他们心服口服,原来就是把我推出去是吧?”
“嗯?老子当坏人,好处全让你占了还不成。”韩铁衣怪道:“要不你给我出个更好的主意。”
“……”吴征无语凝噎,叹道:“人长的帅就是麻烦。”
“……”倪妙筠张口想鄙薄两句,终是被这人的自鸣得意与奇怪脑洞也搞得无语凝噎,只能从鼻腔里哼了一声,心中暗道:怎地忽然会扯到长相上面去,定是脑子有毛病和常人长得不一样。
操演陆陆续续结束,军士们又集中在校场上,结果已然很是明显。
这一次韩铁衣没有起身,吴征第一次站到了众军之前。
还是第一次做主将站在点将台上,吴征脱下衣甲,摘去头盔摆放好了,露出内着的天青色长衫来。
除去衣甲头盔,便不是以主将的身份,但内里的长衫飘逸出尘,才让人又记起他的另一重身份来——昆仑派掌门。
“实话实说,从前我真不屑与你们这些人为伍。我在昆仑山修行的时候,在大秦为官的时候,与你们都不是一类人。占山为王是贼,是盗匪,横行乡里的也都是些没用的纨绔,废物。从前我瞧不起你们,一点都瞧不起。总觉得是怎样的一群人,才能堕落至此。不过我也没有要与你们这类人为难的意思,只消不是犯到了我头上来,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吴征低头,珍爱地弹了弹身上长衫的皱褶处。即使昆仑已不复从前的威名,可于他而言铭心刻骨,也仍为之自豪:“只是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也会和你们一样。大秦对我百罪加身,要将我剁成肉泥。世人讽我败家子弟,甚至是丧门星,才给昆仑派带来灭门之祸。
哈哈,于是我和你们一样,都成了戴罪之身,还有不成器的二世祖,纨绔。”
吴征摊手摇了摇头,又道:“所以,我才真的放下了从前的架子还有优越感,平心静气地看你们。这里的每一位都是我向陛下启奏请来的。额,倪监军不算,她是自愿来的,想来是怕我偷懒。”
“哈哈……”吴征本就甚少架子极具亲和力,何况那一身本事是实打实的,一番话说得有理有据,能与这些从前的山贼与纨绔们说些掏心窝子的话,本就让人心生好感。
再调笑两句军中唯一的女子,还是绝美的女子,不由就惹来一阵哄笑。
“看完了才知道,呵呵,哪来的多少分别?”吴征挥手左右比划道:“都是一样的人物,相似的遭遇,偏生从前搞得自己像是个大户人家的正妻,看着那些填房,通房丫头,乃至半掩门什么的一脸鄙夷,惹人笑话了你们说是不是啊。”
“哈哈哈哈……”
军士们笑声更大,却听吴征沉下脸道:“众口铄金,世人都是这样。你们每一位所受的冤屈,我都记得。若是天生的恶人,他进不得这座军营。你们会来这里受委屈,是因为你们不是天生的恶人,都是被逼迫无奈,即便如此,你们也没有胡作非为,行事有底线。所以我把诸位召集起来,就是想告诉那些冤枉,瞧不起我们还要说风凉话的人,草你奶奶的,针没扎你们身上,凭什么替老子说不疼?”
一句话几乎说到了军士们心坎里去,行走在阴暗之间的日子没人好过,放荡形骸的醉生梦死也不是本愿。
谁又愿被人指着鼻子骂狗贼?
吴征遥指大秦道:“昆仑派上下一门忠魂归天,坑害了他们的人还在逍遥法外。其实,若不是陛下收留我,我也只能和你们一样,要么占山为王,要么醉生梦死。其实,我还年轻,一定比仇人活得命更长。我本可以和你们从前一样,逍遥些,活得爽快些。可是蒙陛下青眼,我也不愿就让那些仇人颐养天年那么好过。
我不肯认输,所以我来这里,一为报陛下收留与信任之恩,二为还昆仑一个清白公道。可是如今,陛下自己也不好过。你们都是土生土长的盛国人,当比我更清楚百余年来,历代先皇委曲求全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谁。所以,我想告诉诸位,陛下给了你们改头换面,洗清沉冤的机会,你们,又愿不愿意为陛下讨一个公道,为自己要一份前程,为子侄留下个光耀的门楣?还是,你们愿意做亡国奴?”
吴征越说声音越大,运起了内力声震荒野道:“留在这里,代价会很高昂,今后会流很多血……所以,今日这些话说完,我不再勉强你们,也不再设任何障碍,如若还想走尽可以走得。我只想告诉诸位,即便今日之后,我是唯一一人,那也没关系。”
吴征拱了拱手施施然落座,他知道不会有人走,即使心不甘情不愿,从今日起营中的每一位都会留下来。
男儿都有血性,吴征的一番话正成功地激起了他们的血性。
霍永宁选择的都是亡命之徒,所以暗香零落只能以威福镇压,永远都是贼。
吴征的选择反其道而行之,所以这里的群豪,就算功力差了些,却可以成军。
他闭上了眼,看似不愿面对可能有人离去,实则智珠在握。
偏生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与他过不去道:“吴掌门所言倒是有理,只是话里话外,是欺我盛国无人么?”
吴征开始头疼,倪妙筠几日不搭理他,这一开口就善者不来,不知道她要玩什么花样。
这女子可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单纯仙子,从装扮上便小心思十足,且极为爱美,穿着打扮都极具个人风格。
这样的女子都是极有主见,心思玲珑剔透的主儿。
何况这一位可是每每被师门赋予重任,极善隐匿藏行,若没有颗七窍玲珑心,哪里办得来这些事?
“不敢不敢,有些事说了没用,做了才成。”吴征嘴角露出些许笑意,话中有话分明在说:你看看你,说要吃一只白斩贵妃鸡吧,可是就没吃。
耍嘴皮子有什么用?
倪妙筠狠狠瞪了他一眼,看懂了吴征的眼神让她心中略慌,没好气地向韩铁衣道:“敢问韩教官,今日是头名可歇息,余者午后严加操演,对么?”
“当然。”韩铁衣眉头一挑,忍着笑道:“只要是营中人,无论是谁,绝无例外。”
“好。本监军也是营中人,不参与说不过去。”倪妙筠冷笑着朝吴征一瞥,自顾自地点起根青香插入吴征那一根旁边的香炉道:“本监军旁观了许久,多少看出些机关玄机,些许便宜本监军也不占你的。”
这一刻的风明显比方才还要大了些。
青香燃起一缕烟柱,又被大风吹散,香头一点火光明亮耀眼了许多,可营中所有人的目光都只注视在倪妙筠一人身上。
她不理青香烧得甚快,一会儿便短了一小截,只信步下了校场,回头一瞥青香已烧了四分之一,这才忽然拔足奔去。
极少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见过她全力施展轻功,吴征也是第一回,直看得眼珠子都几乎瞪了出来。
刺杀[雪夜魔君]项自明之时,美人如云似雾,如梦似幻的剑法让吴征大开眼界。
犹记得她一剑收回剑鞘反身就走,项自明的伤口处这才喷出鲜血,可想而知她的剑法之迅捷。
要像她一样,每每藏于暗中出其不意地刺杀,不仅要有一手快剑,更要有一身好轻功。
此刻她在大风扬沙之中仿佛腾云驾雾,凭虚御风而行,只眨眼间就没入阵法中,仿佛化作了一阵青烟。
箭雨难不倒她,以她身形之苗条,仅需拧动腰肢便可躲了开去,只可惜视线难以企及,仅能凭想象猜测以她胸臀之饱硕,该当如何藏得身形。
须臾间倪妙筠便跃过箭雨,从枪林间翻身而起,衣袂纷飞,在第二丛枪林处竟踏着枪尖前行,这一身飘飘的浑不受力,又是何等地轻盈。
足踩枪尖非吴征所能为,显是她胜了一筹。
待她一路闪过檑木,用的身法与吴征大同小异。
闪过了檑木,面对巨石翻滚美人居然也伸出白生生的手掌来。
圆滚滚的巨石,苗条的美人,令人担忧别把她给压扁了,便是擦破了层手上油皮,也是让人心疼。
第一颗巨石滚至,倪妙筠手掌一伸一引一带,那巨石路径忽偏,从她身侧滚了过去。
美人奔向坡顶,竟给人生出一种劈波斩浪,当者辟易之感。
天阴门的轻功独步天下,最后一堵高墙于她而言更是如履平地。
倪妙筠施展开魔劫昙步,旋着身儿越飞越高,好整以暇地落在墙顶远望吴征。
被顶礼膜拜了一番,她才跃落墙头奔回点将台旁灭了青香道:“韩教官,是我胜了吧?”
她出发前青香已烧了小半,现下还比吴征的多了一指宽,就算是最后出手占了便宜,优势也已太大。
韩铁衣笑吟吟道:“舍倪监军其谁?在下拜服。”
“嗯,那本监军午后再来监督诸军操演,若是有不用心的,莫怪本监军刀下无情!”倪妙筠又朝吴征冷笑一声,一拂衣袖侧身离去。
只是与吴征擦身而过时,才听他恼人的声音送入耳中:“原来那天你故意追不上我呀……”气得她面色发白,又险些打了个跌,足下加快逃也似得去了。
经倪妙筠一[闹],偶有几名打着小心思想离去的也知不敢走了。
吴征的话里的确有看盛国无人的意思,无论真心也好,激将也罢,人家有那个资本说出这句话来。
而盛国的颜面居然要倪妙筠一名娇滴滴的女子来维护,此时再走,只怕还没走出营门就要被无数目光被盯死,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
谁愿子孙世世代代为奴为贼?
没有。
“这么聪明的女子,了不得,怪道雁儿也肯让她进你家门去争宠。”韩铁衣拍拍吴征的肩膀,用痛心疾首的目光与声调道:“被个女子抢了所有的风头,可怜,可怜。”
“我呸,有本事你去把场子找回来!”吴征心里甜丝丝的,仅有那一点装逼失败的火气全撒在了韩铁衣身上。
“没功夫,你很闲么?”韩铁衣指着校场道:“这叫八门金锁阵,别人有空用饭,你没有,快去看熟了。”
“我……”
晨间演了这么一出跌宕起伏的好戏,军营里热闹起来。
无论是闯阵时的疑难点,还是吴征与倪妙筠显露的惊人武功,都是说不完的话题。
“他娘的,老子就不服吴将军,就服倪监军,你有意见?”胖和尚忘年僧,人送绰号一气呵成,嗓门还是震天响。
他一边呼啦啦地往大嘴里巴拉着面条,一边口沫横飞地挥斥方遒:“一个大男人偏是剑走偏锋,使些轻功过关算什么英雄好汉?你看倪监军一个娇滴滴的弱女子,还是书香门第出身,那一手武功才是名副其实地厉害。老子服气,真他娘的服气。依老子看,吴将军在倪监军面前就是矮上半头,在监军面前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绝不敢说半个不字。否则倪监军要与他比划比划,吴将军只能认栽,你们说是不是?”
无人应承。
待了片刻,面子上挂不住的忘年僧火气冒起,还要[据理力争],于右峥才及时在他肩头一拍低声道:“大师说得对不对在下不知道,只是提醒大师一句,吴将军的话大师最好还是乖乖地听着,否则倪监军会第一个把大师的头砍下来,切记,切记。”
“昂?”忘年僧吓了一跳道:“什么意思?”
“凡俗中的事情,大师是出家人不懂,也不必懂。总之大师牢记在下的话就对了,不信,大师问问诸位兄弟。”
忘年僧铜铃般的眼睛左右一瞪,只见同一张桌上吃饭,平日较为相得的好友大都频频点头,他一摸光头道:“见了鬼了。”果然从善如流,这一下声音就小了许多……
……………………………………………………
相比于寻常人家,皇宫里的金碧辉煌仿佛天上的琼楼玉宇,不可逼视。
而享用这一切的天子,也比寻常人家要辛劳许多。
夜色已深,紫陵城里万籁俱寂,皇宫的御书房里却还亮着灯火。
有了一代又一代暗中呕心沥血的帝王,才能让这个在夹缝中艰难求存的国度延绵至今不破。
张圣杰大大地伸了个懒腰,又狠狠打了个呵欠,饮了口浓茶才站起来身来,混不顾忌天子威仪。
一旁陪伴的费紫凝看得有趣,嫣然笑道:“陛下累了,不如早些安歇?”
“正是,今日差不多了。”张圣杰握起费紫凝的手,让太监们远远跟随不得靠近,出了御书房缓缓向后宫行去。
夜风虽凉,散散步却能让坐了一日的筋骨舒缓,张圣杰一边舒展着四肢,一边道:“吴征连个话都不回,想来还是被吓着了,哈哈。”
“陛下传的旨意这般不依常理,不把他吓着才怪。”费紫凝也忍俊不禁。
张圣杰传口谕时她也在场,倪妙筠惊得目瞪口呆,她也差不多。
可一想倪妙筠去传旨的模样足能脑补出无数种场面,每一种都会有趣得很。
“此吓非彼吓,他怕的是朕到了战场上乱传旨意,不是被那道口谕吓着了。”
“嗯?”费紫凝轻叹一声道:“陛下如此信任吴家,臣妾当真是想不明白,只能叹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倒要敬佩陛下胆色过人。”
“你呀。有话便直说,何必拐弯抹角?”张圣杰对这位贤良的皇后十分喜爱,连梓童都不愿叫,不是直呼爱称便是你呀你的,更显亲近自然。
两人相携的手紧了紧,张圣杰道:“朕也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过朕要先问一个问题,你可知朕为何早早就选定了你为后?”
费紫凝自小就是以皇室储妃培养的,费家对盛国皇室的支持与重要性,也几乎确立了她长大后就是皇后。
可说得再多,必须张圣杰肯答应才成。
张圣杰自幼被软禁在长安为质,又从哪里通晓一名女子?
此事费紫凝不好意思问,倒是心中也屡次好奇。
“臣妾听陛下指点。方才是臣妾错了,陛下也不需与臣妾拐弯抹角。”费紫凝调皮地吐了吐舌头,显是对张圣杰也发自心底地敬仰与喜爱,甚是相得。
“我在长安时明白一个道理,要了解一个人,首先看他周围的都是些什么人,怎么待他,再看他落难时,周围的这些人又是怎么待他。”张圣杰十分感慨,思绪仿佛飘回了饱经苦难的过去:“凝儿在费家就喜好读书,谈古论金极具见解。
又生性简约,御下平和,甚得朕心。这一切若只是凝儿如此那算不得什么,世人多有面善心恶之徒。可凝儿身边人也是如此,则谁也做不得假。朕选中凝儿结为夫妻,堪称平生得意之举。”
费紫凝听得心中甜丝丝的,羞红着脸道:“臣妾谢陛下夸赞。”
“据实而言,不是夸赞。”张圣杰长出了一口气,仿佛吐出所有烦闷欣然道:
“引吴兄入盛国,也是得意之举。你且看他身边都是何人,再看他落难之时,第一回落难,身边有个杨宜知尽心尽力,同门也没人待他多严苛,这一回落难,昆仑可谓根基尽丧,可是多少家族跟着举家相随一同入盛国?”
“昆仑里都是世家子弟,这些人都不是凡俗之人,吴征平日人品如何可见一斑,陛下果然慧眼如炬。”
“呵呵。可笑大秦痛失柱国之材,梁兴翰识人之愚,还比不过会在青云崖旁陪伴吴征的区区一个杨宜知!当然了,朕之所以对吴兄全无提放,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个原因。”
“臣妾愿闻其详。”
“凝儿与吴兄也见过,有没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张圣杰搜寻着一切词汇,艰难描述道:“有没有觉得他似乎,看朕的目光很不同。没有那种畏惧天威之意,他很平和地看着朕,当朕就像一个普通人?也不对,总之就是,他并不羡慕这个帝位,也不怕天授的君威。也不对……哎,朕不知怎么说才好……”
“臣妾能懂,臣妾确实也有这个感觉。”
“那种感觉,就像朕把皇位送到他面前,他也不会要的。他会嫌麻烦,累…
…呼,朕也看不明白他。”张圣杰又吐了口长气忽然哈哈笑道:“所幸吴兄是个忠孝信义之辈,才肯为了还昆仑派一个清白,讨伐仇敌而委身盛国,否则现下他指不定已鸿飞冥冥,不知远去何方了。也所幸吴兄的根基不是帝王之资,天下三分也没了插足的地方,否则他也可能自立旗号,不假手他人了……以吴兄之才,若非不具天时,他做得到的。”
“原来如此……正因如此,陛下才一直与他兄弟相称,陛下与他更像是合作,而并非是臣属,对么?臣妾口不择言,陛下莫怪。”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凝儿!”张圣杰舌颤莲花大赞了一声道:“果然聪慧伶俐,凝儿一点就透。”
费紫凝的脸红了起来,爱郎的称赞足以让人脸红心跳,此时又已接近寝宫,陛下的心思她当然明白。
果然张圣杰的脚步加快了些,握着的手也更紧了些,像是防着她逃走,一脸喜色,又低声道:“凝儿的准备如何?”
费紫凝心中一凛,也低声道:“臣妾生是陛下人,死是陛下鬼,陛下去哪儿,臣妾也去哪儿。”
“嗯……没有多久了。”张圣杰依然笑嘻嘻地,几乎已将费紫凝搂在了怀里,声音更低道:“破釜沉舟一战,不仅御外敌,更需肃清朝堂,此事危机重重,凝儿也要受苦了。”
“陛下自有天子鸿运,不必担忧,至于臣妾生死不渝,若有不讳,亦不独生。”
费紫凝满面绯红,虽觉张圣杰的行为即使只是做给人看的也十分不妥,却不由自主地靠得更紧了些。
“嗯,还有花贵妃,她是文弱女子,一同出行凝儿务必费心照料。军营清苦,今后颠沛流离的日子恐怕少不了,怕是长久难以享得片刻安宁。今夜不如……”
“陛下。”费紫凝皱着眉嗔道:“妹妹处臣妾自会照料,只是……不是臣妾善妒,陛下的龙床上只得一名女子,若是陛下要召妹妹来,臣妾可为陛下代劳…
…”
“额……”张圣杰绕了好大一个圈子,布下重重迷阵,仍是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尴尬道:“那也不必……花贵妃就明日,明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