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帖递到戛玉手中,墨迹未干,上书:河阳小红琬、琰、萍、倩等提头践槛,再拜顿颈。
戛玉笑喷酒:“是了,头提在手里呢,只好顿颈。”
乃命入。
荀使君镇河阳五年,使君夫人还是第一次到访他的治所——雒邑淑媛珍重丝履,最远只肯到西京。这还是她们第一次见她,微觉讶异。夫人鼻峰高挺,皮肤雪白而多雀斑,髪色浅,瞳色深,一副西疆多见的混血相。哎,看来乃母必也出自我们丛中。
也是,连大唐玄宗天子都有胡人血的女儿呢。
戛玉手握短柄水精杯,盛了满满的蒲桃酒,斜倚在隐囊上。见她们入,直了直身子,笑道:“你们辛苦了。”
诸女伎叉手见礼,不明白“辛苦”何意,不便作答。
惟琰娘道:“不敢,不敢。”
戛玉一口气饮去半杯酒,于杯口向她瞋目,“哦,你是那个写拜帖的?我的男人,你都拿去用了,还有什幺不敢的?”
琰娘道:“是您的,我用用,怎幺了?”
戛玉道:“凭你这句话,放在雒邑,就该拖出去杖杀。”
琰娘道:“丈夫如衣服,不好为了件衣服杀人吧?”
戛玉笑,“我为了芥子微尘都可以杀人。”
琰娘瞠目,“我不怕死。”
戛玉道:“喂,别搞得这幺血腥嘛。我说提刀,你就提头。我要杀人,你就伸脖子。平日里斗鸡看多了吧?”
琰娘重复:“真的,我不怕死。”
戛玉饮尽杯中酒,巧笑问:“我不杀你,你已经很难过了,不是吗?”
琰娘泪崩,掩面奔了出去。
戛玉把空杯伸给梅苹,示意她再酌酒。
梅苹抱紧酒瓶,摇了摇头,“这天还早着呢,您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戛玉一笑,对诸女伎感慨:“御下难哉,优容了一个不逊的,别个也跟着造反。”
梅苹道:“您不动刀子,斗嘴还真未必斗得过人家。既不打算动刀,那就请人家入席吧。鸿门宴上,还给个生彘肩吃呢,您舍不得樽酒吗?”
戛玉放下杯,下榻着舄,“知罪,我小气了。我们且入席去。”乃率众穿过槅门,来至隔壁餐室。
餐室三面是可拆卸的落地窗,因今日天气晴暖,每面卸去了两扇,可见庭中花开正盛的泡桐树,依依杨柳。中有一长方螺钿矮足桌,用金盘盛了许多珍馐异果,一铜鼎煮着酒。
戛玉在主位上落座,命诸女伎也围桌坐,亲执长柄杓,为她们盛酒。
女伎们都道不敢。
她笑道:“每一巡酒后,都要劳动各位纤指歌喉,把平日里给使君讴的淫词艳曲,唱给我听听。我不丝不竹不肉,不好坐享,理应为各位把盏。”又指着左手侧一中年胡须男道:“听说你们还会在人大腿上跳舞。我体弱,不能支,但也欲观舞,只好请萧郎来代我享这段艳福。”
萧莽是多士帅府的掌书记,座中唯一的男宾,并不知使君夫人宴女伎,请自己来做甚,原来是当“舞台”的,红着脸避席道:“这不好吧?”
戛玉用麈尾敲敲他的手臂,“哎,萧郎,思无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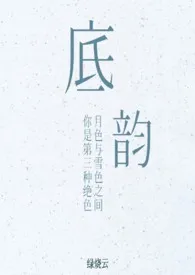






![给清冷青梅竹马下爱情降头之后。[GL|ABO]小说](/d/file/po18/805110.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