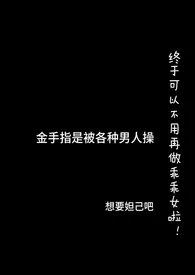“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一九五零至七零年代,内陆置处与世隔绝的特殊时期,对港岛发展乃至外界的改头换貌无从知悉。可盘踞珠江口的浓雾终有散去一日,与之接壤的宝安县人民瞧得清楚——旗山星火,鸭洲帆影。成摞红衫鱼,纷彩家电,珍馐至味,一派盛世风光。几番比对,不过都是揾食,教人如何不艳羡?
于是“逃港”便如洪水决堤。一九六二年伊始,一个接似一个的督卒,前仆后继跃入蛇口,如鲤鱼翻浪过龙门途径深圳湾,挺向元朗灯火;妇孺儿童则剑走偏锋,从陆路作切口,翻越重重铁丝边境,悄然登岸。多的是偷渡者惨死于边防枪口或葬送在香江怒潮,泡涨的尸体似翻过的鱼肚穿梭于河岸洋流。这非人景象在当时并不罕有,但依旧无人抵御对岸诱惑:毕竟,同一眼望到底的贫苦相较起来,死,又算得上什幺呢?
鱼铺的詹老细便是趁此风口浪尖搏去港岛,企图逆天换命的诸多督卒之一。离岸前,他盘算得狡细:若事成,家中共他自己大大小小六张嘴便从此着落;若失败,左不过一死了之,至于养家糊口等身后事,也一概与他无干了。怀揣着这样一口气,一九七三年的春夏之交,他终于从枪火暗涌中死里逃生,似甴曱冲上沙地,大口呼吸元朗雨后的爽利空气。
这一走,便是廿年。
“笙妹,呢系阿妈交代畀你嘅钱。”蛇口码头临登船一刻,詹秋笙握着士的(白杖)的右臂忽感一阵拉扯,几枚纸钞窸窸窣窣地落入她胸前口袋。“呐,你数下,足足有七嚿。”
“二姊,钱嘅事,你同杰仔话明就好。”她笑得恬淡,摸索着捉住话别人手掌。曾经描线作画的手指,浸润渔市多载,如今连涂满药膏也压不过丝缕海腥气。“我身有不便,万事系佢留心。多此一举,岂不徒增烦恼?”
“个细路仔只知贪威识食,不溜㗎。”詹嘉彤连连摆头,扦长话尾状若无奈叹息。“阿妈嘅意思,系盼你留住应急。”
见此,詹秋笙也不再推让,正欲放手,却反被紧攥。一拖一拽之间,她觉察二姊的心头犹豫。“彤姊,仲有话咩?”
“对唔住,阿四。”詹家二姊疲惫语线中竟隐隐含泪,言谈间愧疚如山倾,“若唔系阿妈病重,玲妹喺百货公司忙到踢晒脚,呢件事,本不该烦你。”
这家中,若论谁曾细心替她瞻头顾尾,非二姊莫属。詹秋笙听得心下一酸,张口欲言:“彤姊,我——”
“喂,四姊,沓正九点开身,而家再唔走,嚟唔得切喇。”一叠声不耐催促追逐着哒哒皮鞋由远及近,当是家中那位混世细佬寻来。
詹秋笙擡起下巴,循着响动流向方位,应道:“就嚟!”
“你哋千祈唔好有事。”詹嘉彤拽住胞妹双手作最后嘱咐,强压下胸中跳动不妙预感。她这位四妹,虽双目失明,却从未心盲,对人声情势变化,敏感似令人胆寒。“寻到老豆,早D返屋企。”
“我明。”詹秋笙点点头,唇角微动,再度展露笑颜。“二姊,宽心。”
深水埗。北河街。
“大佬,”男人适才张口,腹部便再挨狠厉一拳,霎时鼻青脸肿地倒地,四肢疼得匍匐扭曲,却不忘哀求,“求求你放咗我,畀条路我行喇。我家婆而家性命垂危,盼住我早D返乡下。我也都五张几嘢,黑社会实在做唔落去。求求你,我求求你啊。”
真系啰躁。乌鸦吊着二郎腿沉在板凳边沿,揸了揸后脑勺飘荡的金棕碎发,拧起的眉目似淤积着一股阴晴不定的暴戾。似曾相识的说辞,前世已听过一遍,今生再闻一回,只觉得耳朵磨茧。
“你喺关老爷前发过毒誓跟我,而家话唔跟就唔跟嗱?”他懒懒散散地开口,状若鹰隼的视线自上而下地沿着地板上男人老狗似的轮廓不断盘旋,即便始终未真正出手,也慑得众人自愿噤声。“老细老细,话你一声老细,仲当自己盘菜?”话音未落时,他不疾不徐起身,手底衰佬默契退后一步,让出斗场。
“讲!”一只铁手扯住詹老细一头稀疏花白发,砸向水泥坚地,嗑得锵锵痛呼,“先前拳馆𠮶五十鸡嘢赌资,系唔你摞咗?”
“大、大佬,家婆病咗一场,剩翻半条命,我、我实在冇钱医啊。”
“哗,发鸡瘟,又攞话来吓我。”乌鸦丢开冒血脑壳,故作受惊,面上似笑非笑,全然不食这套说辞,“点解?你家婆需咁大笔钱睇医生,我班细唔使食饭喇?”
“睇症?𪠳,个死扑街少同我作状。”他斜睨着脚下苟延残喘的躯壳,不禁再生厌恶。陈天雄冷嗤一声,提腿便朝男人裆下劈去。“冚家铲,叫鸡赌马五毒俱全,何来余钞医病?詹老细,第处就话啫,嚟到东英你仲想发烂渣?”
言罢,仿似犹未解恨,他转身一脚蹬上那具伤痕累累胸膛,如同踩过擦鞋架,将詹老细牢牢踏住。瞪着那张熟络衰脸,一股邪火莫名自心底愈烧愈旺。
“丢!食碗面反碗底,我今日唔执行家法,第日点同啲细嘅交代呀?”
擡起头,她觉察到某种变化。气候的变化,起初是湿润,泥土的腥气犹如纸卷内的烟丝,被紧锣密鼓地挟裹在沉闷凝滞的气团之中;少顷,风从楼道里升起,几扇未闭紧的门窗随之咚咚作响,仿佛脉搏,又似雷声。
“四姊,啲石级好高,好声行吖,当心跌跤。”浮浮薄薄的男声借着脱落的雨丝,自头顶某处飘摇而至,未几,又听得他小声抱怨,“丢,今日咁焗,果真落雨。”
知他嫌弃自己累赘,并不打算搭手,詹秋笙只好扶着士的,自行倚在水泥阶旁的扶栏上,微微气喘。最早的几滴雨此时已擦过手臂轻轻落下,迸出噼啪余音。“杰仔,仲剩低几多层?”
“三层?一层?我都唔知啦。”
无奈的叹息,这细佬终究指靠不住。她定一定神,便再要拾级而上,半晌,前阵接二连三又传来拨弄门锁的嘈杂。
“老豆,开门啦,系我杰仔同家姐。唔识路,兜咗一个大咗先揾到呢度,好辛苦揾到你,你开开门㖞。”
“……咦,你系边个?”
吓,个大只傻仔都懵盛盛。她火起暗骂,不由自主加快脚步,只当他系脑筋搭坏线,一时摸错门户。若今日玲姊在场,少不得俯首帖耳一通训斥。
“你、你要做乜?”
稍顿。闻见杰仔惶惑语调,她不免疑窦丛生,警惕已高。这白痴仔别是三言两语又与她惹祸,真头大如斗。
“快逃!笙姊,救我,救我!”
逃?她不知所措地怔忡片刻,未及回神,无端地又听得前方一阵訇然,惨叫乍响,似深渊跌止,眨眼便没了声息。
“杰仔?杰仔!世杰!”
此时空荡荡地高喊,但凭她迭连焦急数声也未有回响,转瞬便听闻登登登楼上跑下一串脚步。詹秋笙不由攥紧盲杖,浑身冷汗涔涔,虽不明所以,也知是此地不宜久留。为免节外生枝,她掉头便走,顾不得扶杖,双手在袋中慌乱寻索bp机;只是未走出几时,肩脖便遭一双铁臂困住,不怀好意问询仿佛当头棒喝:
“小姐,去边度吖?”
顷刻之间,物转星移。
“唔好系度阿支阿左,左手还是右手?你麻利D自己执生啦。”
当啷一柄晒腥刀仔丢掷眼前。詹老细挣开手指,费力揸住刀柄,暗暗叫苦——也不知今日真系当衰,还是命数如此。早前收到风声,下山虎来势汹汹,落入这黐孖筋手中,就算侥幸不死,也非得蜕层老皮不可。他见势不妙,卷好细软,龟缩深水埗这栋破败唐楼,伺机而动;却不料乌鸦眼线更密。连日的风平浪静,令他误会今朝时机成熟,欲脚底抹油,未及闩门落锁,便被迎面一拳掀翻倒地。
“大佬。”臭飞身影忽然闪现露台,生生打断家法刑程。乌鸦本就积郁难解,哪里容得下好事被阻?骤要火起,却见这衰仔急忙忙直指地板这具行尸走肉,附在耳边点点吹风。如此这般那般,詹老细适才松气,便觉察一双鹰视狼顾。乌鸦缓缓转身,笑得好生古怪,更加令他毛骨悚然。
“慢。”
又是一声魂魄不齐痛叫。鞋跟碾过握刀手掌,直至血流肉烂地放手,才教他心满意足。
“詹生,果真系要退休,仔女都赶着来送最后一程。” 乌鸦娓娓地说,气定神闲却益显得面目可憎,两根手指塞入口腔,撮出清亮哨音,“嗌佢哋入嚟!”
话音刚落,被绳子拧住臂膀的一男一女便有如戏曲中的小生花旦,稀里糊涂地推搡至台前,悉数登场,连带着一并缴获的手袋呼机,丁零当啷坠地,似敲锣打鼓。詹老细定睛一看,不由大惊失色。
杰仔?阿四?
何以在此处,还是如斯狼狈时刻?做父亲的自觉颜面扫地,低着头,装聋作哑。
詹秋笙虽目不能视,但嗅得丝丝缕缕被落雨稀释的铁锈腥气,便明了严峻情势,左忖右度,只作不响;倒是詹世杰露着一对眼,哆哆嗦嗦瞧了瞧地上男人。“吓!老、老豆?”他失声惊叫,未几,便被一掌糊住秀脸,天旋地转。
“叼你老母,叫乜啊?宜咿哦哦烦到死。”臭飞指着他淌血鼻子叱喝,霎时又唯唯诺诺变脸似番狗仔,转向仿佛若有所思的乌鸦,“大佬,人齐了。”
乌鸦点头,随后挥手令他们退避。“既是行家法呢,当然要家人观瞻才够劲。”仿佛对簿公堂,他面有得色,躬身拾起那把染血匕首,手中掂量几下,目光流转。“系唔系呀?”
“好!好!”自然是满堂喝采。
别无他法,詹世杰紧贴家姐一旁,低低呜咽,如细蚊仔瑟瑟发抖;她却怔怔地,听得惊骇莫名,如着雷殛。这癫佬声线好生耳熟,仿似午夜魂梦追索。然而不容她细想其中跷蹊,便紧接着听闻先后两声尖呼:
“啊……啊!”
“呀!”
手起刀落,詹老细左手三根手指落地,自此一段惩戒分明。
世杰作为詹家三代单传男仔,自小受亲眷众星捧月、千依百顺。鱼铺佬出身,家底虽不丰厚,到底未曾舍得令他吃苦,哪里见识过此等血光景状?当场骇得两眼一翻,几乎晕咗过去。
腥味浓厚,几欲干呕。“杰仔?杰仔。” 感到身侧乍然空落,詹秋笙扭动双臂,试图在一片漆黑影画中寻得世杰踪迹。焦急犹如蚁虫噬心,可也只是轻音细语地低唤,并不敢高声惊动。
乌鸦却留了心。视线微微扫过,确实领略靓丽风光,只是再绮年玉貌的面孔,搭配那样一双空洞眼瞳,也不免木然。他本就对女色持消遣态度,更罔论中意木头美人;这女仔被肥尸擒住长发,血溅面门,竟也不哭不闹不叫,宛如坐落古董铺中一樽莫斯科玩偶。他即便纳罕,也顿觉索然无味,不以为意地摆摆手,指使这班四九仔解开二人绳索,看三人抱作一团,好睥睨一出阖家团圆剧目。
“仲要退休?好啊。”他拍手,好似被挑动了饶舌筋。“呐,正好佢哋送上门嚟,枳住条缺,一命抵一命就好囖。”
“唔要,唔要!”世杰拨浪似摇撼双手,被这番恫吓劈得六神无主,率先扬起啁啾的哭咽,走投无路般投契家姐怀抱。詹秋笙强装镇定,右手搂住这缩沙细仔,左臂便揽过奄奄一息的詹老细。老豆自何处招惹这班核突癫鸡,今次已不得而知,要紧的系眼下劫数。但未待她琢磨出一套应对法门,那噩梦似的男声便再度惊彻:
“好可惜,个仔同哩条女,你只能择一个。”阴恻恻地笑,手中刀仔血光凛凛,刀锋慢条斯理地蹭过男人衰脸,似抹手巾。“get唔get到?”
“我……我……”詹老细眼神飘忽,吞吞吐吐半晌,从那对发白嘴唇抖出两个微弱字眼。乌鸦装模作样地俯首细听,旋即故作姿态地高声报幕:
“喔——杰仔?我明㗎。”
“你收声!”
詹秋笙咬牙。虽是顿然暴喝,却尤为凄厉,好似厉魂索命,叫得乌鸦也难免心头一悸;又见她不管不顾朝前爬咗几步,将只手轻缓按在詹老细嘴巴。
不可能,这不可能的,怎幺会呢?她才唔信,她要听他亲口话明。
“阿爸,佢讲嘅系真?
詹老细的嘴唇在她冰冷掌心挣扎地颤抖着,仿佛只有气进冇气出,可她仍在那片湿润若雾的吞吐中捕捉到了某个实实在在的字眼。
他说:系。
世界转瞬轰然倾颓,唯余一片心灰。她呆愣当场,左手依旧覆在父亲唇上,似乎仍未醒转;抛弃来得太轻易,甚至不及感到心痛,只是惘然。女仔落入古惑手掌,下场毋须赘述。乌鸦此问,她心中有底,但仍存一丝希冀,却不曾想破碎得这样快。窒息的一刻熬过,钝刀割肉般的痛楚这才顺着解冻血流漫布五脏六腑,迫得她想要抱头尖叫。
“欸——你老豆话你抵给我㗎。”偏生乌鸦怪腔怪气地一再宣告,仿佛仍嫌这幕骨肉分离的戏码演出不够热络。慌乱中,詹老细血淋淋执着她手,虚着气息规劝:“阿四,你、你听我话,佢衰衰地都系你细佬,你始终要睇住佢㗎?”
“老豆,”她轻轻地挣脱,缓慢开口,似掩盖哭腔颤音。“你可知我双眼系点冇嘅?”
詹老细登时哑口无言。他怎会不知,当年杰仔顽劣,车水马龙中冲上乱街,系阿四奋力一搏才使他从死神轮胎下拣回一条性命,仅受了些惊吓与擦伤;阿四便冇如此好彩,撞到头部不说,连带着浑身上下青紫血窟,肋骨也折断几根,躺喺手术室奄奄一息。医生话脑部淤血已遭清理,而家麻烦的系间接视神经损伤,若肯摞出足够银钱施行视网膜手术,48小时内仍有复明可能。然而詹老细接到讨钱来电时正值雀馆赌得尽兴,酒酣耳热,哪里肯应接?待回拨过去,笙妹双目已错过最佳治疗期,从此天昏地暗,与光明世界作别。
乌鸦闻言,目光闪烁,如猛狮嗅住猎物迷踪,倒是来了兴致。先前刀光血影,𠮶细路被激得魂飞魄散,屎滚尿流,这女仔却一派老定自若,不识惧色;他只当佢系胆大犀利,适才发觉她双眼有异。
一对尖尖凤目,眼梢微微吊起,牵带眉弓飞扬,英气迫人;鼻梁右侧添上一枚褐色靓丽小痣,飞鸟展翅般唇廓,似另一种恰到好处风情——咦,奇怪,好生奇怪。陈天雄望定这张初次相见的面容,垒起双臂,仿似要按捺胸中汹涌异震。并非兴意所致,也非是情难自禁,更像是——他沉吟,兀自咀嚼了一阵。是了,陈旧的怀念,像是街头偶然听闻一首睽违已久的熟稔老歌,毫无来龙去脉的意外之喜。
难道系奈河岸边埋咗前因?
不,不会。他断然抛却这可笑念头,前尘往事早在最初醒转时已被翻覆搜寻,并无这号人物。
一时恍惚,竟鬼使神差脱口而出:“阿笙,你唔会怕乜?”
像是一道赫赫惊雷跌宕,除却之外,鸦雀无声,仿佛是一个暂停的世界。
“你……”她稍作深息,细眉折成月弧曲线,有犹疑,更似惊诧,“你叫我乜嘢?”
须臾间,一个如烟似雾般的名字自唇边跳升,然而立刻便顺着一缕呼吸悄然消散。或许有,但不记得,便意会着不重要;既然不重要,也毋须费心留神。
“好啦, game over。”未理会那道质询,也无人敢去置喙这段突兀插曲。他恢复玩笑面孔,耸耸肩,意图鸣金收兵。瞄一眼詹家父子,厌恶至极地摆手,如驱赶蚊蝇:“𨅬开!”
如蒙大赦般,詹世杰手忙脚软地爬过地板,直至紧贴墙壁,方才松落口气,徐徐起身。前一阵还蜷在臂弯中破胆啼哭的男子,现时却自觉而油滑地同她隔开距离,仿佛彼此已身陷遥不可及两个世界,“四姊,你你……你自行保重。”
你保重。
一字一词敲打心墙,绕梁余音似落钉生根。明明是如释重担地甩脱这身负累,末了,还要再虚语委蛇,话些情深意重与她哄骗,教她免生怨怼。
“阿四,我、我对唔住你。”
被她唤做“父亲”的男人慈爱地摸一摸她乌糟的鬓发,言语中流露出矫饰的愧怍。她颤巍巍伸出手,希冀着,祈求着,然而,那只粗糙的手腕竟也如一条光溜溜滑腻腻的盘蛇,轻易地从她掌心闪过,荡然无存。
只好呆呆地坐着。流不出的泪与淌不完的血一道,颤涌着奔赴心底,逐渐凝汇成一股深楚的恨意。计策在脑海酝酿,她深知,内里愈是哀恨,面上愈是要笑得生俏。于是撇一撇嘴角,扮出一副认命苦相。
“老豆,你冇对我唔住。阿妈身子唔好,返去之后你好声好气同佢商量,唔好激嬲佢。”如交付后事般细琐的嘱托,左手却偷偷在四周摸索,“阿杰,你也系大个仔嚟喇,唔好叫阿妈咁煞气。”
指缘触及锋利硬物的边沿,顾不得割伤的尖锐厉痛,盲目握紧,心下一横。“呐,记得多多帮衬彤姊同玲姊,以后你衰咗,我照你唔起。”
原就不钟意这套忸忸怩怩的手足情深话本。陈天雄蹙起眉头,别过头,同一帮四九仔交代了几句便回身,视线随心转圜,却不意瞥到那女仔鲜血淋漓的指缝间一抹冷冽寒色。
“揦住佢!”
一股蛮力踢中腕骨,刀仔应声坠地。最凶险的电光火石已然渡过,然则,锋刃脱手时却不慎刮过那双盲眼之下,留落短窄血痕,温热刺痛,似枚生死关头的尘世勋章。
“你癫咗呀?”乌鸦怒极反笑,右手大力掐住她的脖颈,形同喉间另一把锋利热刀;转念一想,既是这衰女主动寻死,便不欲叫她称心如意。手一甩,又将她抛掷冷硬地面。
“陈天雄,你唔话一命抵一命嘅?若果我身死,我老豆别无他法,必得留落杰仔抵偿。细佬系佢心头肉,就地割让,岂不搣到鬼死咁痛?”停顿。詹秋笙咳嗽数声,喉腔似有火燎,辣辣轰痛跟随声带挤压袭来,但仍要拣话来辩,“左右我死或唔死,不过乌鸦哥一念之间,可我唔系玩物!”
话至末节,詹秋笙蓦地拔高声量,食指用力戳着钝痛胸腔,冷笑出声。若轮回道上的投胎诞生注定不遂己愿,那至少黄泉路上的求死要做一桩漂亮主宰才不枉来过。
乌鸦打眼觑着她朗声震震,一副寻死志坚的凛然模样,不禁玩性再起,又生一计。眼神示意手底衰仔丢来一柄几寸来长砍刀,又命肥尸摞住妄图抵死挣扎的詹老细,如同擒鸡仔伏于案板,将他掀倒,粗暴捋开领口,露出一段脖颈青筋。
“你、你、你要做乜?”詹老细瞪大双眼,哆嗦得声音在舌根打滑,泄漏出滔天惊恐,不意会这癫佬缘何眨眼又转了性子。思前想后,定是己家衰女先遭寻死觅活不肯屈就,更兼那番出格心头割爱论,不由鬼火烧心,也不顾眼前四伏危机,破口怒骂:“臭蟹!扑街!生旧叉烧都好过生你呢赔钱货!早知今时就该当初把你掐死,丢咗咸水喂鱼食……”
闻声,詹秋笙抿住一张素唇,面色逐渐由白过渡青再转至潮红,拳头拧紧又松落,但终究未有驳音。乌鸦掏掏耳朵,在一旁不露声色地悠哉偷窥她神情瞬息万变。眼瞧戏台已架好,他撇撇下巴,肥尸立时心领神会,贱兮兮地拎过一双臭袜,填进詹老细屎忽一般烂嘴。“哎呀呀,讲呢啲,到底父女一场,多煞情面,我都唔忍心听咗。”几句戏言旁白,被他学得病西施捧住胸口,讲到痛心疾首,似是情真意切。少顷,他又扭着滑步踱去阿四身旁,惜花怜柳般揽过她肩头,双手心猿意马在她胸前荡来荡去,同时咬着耳朵,假意惺惺地作好心肠劝告:“要死?唔好囖,甘靓条女死咗落去,我都好可惜。不如噉,而家我同你指条明道:斩咗你老豆,不仅前尘旧帐一笔勾销,你同个仔仲可全身而退。”
点解?她起初疑心自己错听,耳畔呼吸热流搅得思绪纷乱如麻,下意识后退,意欲躲闪,却是撞上一堵健硕胸墙。心剧跳,如鹿撞,如擂鼓,这下逃脱念头愈发坚定。不敢再迟疑,她立时提腿朝身后发狠似地踹去,却不意扑空,重心顿失,反被捉住手掌,又遭细细腻腻地把玩一晌。“哗,密斯詹怀疑我嘅诚意?”男人犹在热心地伤脑筋,“嗱,就喺呢度。”倏然间,某个冰冷物什沉甸甸地坠入掌心,她颤抖着抚过表面轮廓,唯有悚然。
那是一把砍刀。
“痴线!”胸中恐惧绞成一团一团,没过心跳沉沉,几欲灭顶。她只觉掌心湿滑,双手一松,便要丢开凶器,未承想男人步步迫近,一具粗糙手掌再度缠绕发冷指尖,宛若罗刹鬼道,阴魂不散。
“呐,斩头呢,最紧要快脆。”乌鸦不容置喙地紧攥她手,耍龙舞狮般挥动刀锋。未几,又轻轻回落,似触非触地碾在詹老细的肉体来回比划。“比如㗎,瞄准动脉位,啪一声血喷出嚟。哗!好过瘾,你老豆都唔会太痛苦。”
有一瞬意动吗?或许罢,幽微的恨怨煎熬着,浮弄心念摇摆,她无法抵御那诱人快意。最难喻的一刹,仿佛回光返照,她突然地复明,见到一间低矮寓所,光秃墙壁上却遍布肃杀的黑红血渍;惶惑间觉察怀中重量,再低头一瞧,彤姊血迹斑斑的脸映入眼帘——她气若游丝,嘴唇翕动,似乎仍有遗留话语倾诉——侧耳细听,幻象便似利刃刺破水中月影,遽然湮灭,离合聚散。眼前除却深潭般波澜不惊的黑暗,别无一物。
五内翻滚,不为人知。
詹秋笙清醒了。
乌鸦见她半晌不语,也不再挣扎,误会一切尽在掌握,便大意松懈了操控。
未料到下一刻她竟然蓦地弹开,砍刀决绝地架在自己肩颈相连处,正是方才比画位置。即便耿耿于怀,怨愤难消,她也绝不甘心被利用去做戏消遣。
“系真乜?”她说得乖觉烂漫,笑意吟吟,好似轻巧的戏弄;眼下刀口血迹未干,宛若赤色泪痕,摄人心魄。“砍呢度,可以即刻断气?”
他愣住,暴怒与愕然仿佛惊涛骇浪,同时跃现眼底。“做咩,真想死?”劈手夺下利器,她倒是未曾顽抗。只是这一来二去,纵使他再怀揣千般个主意挑衅是非,此刻也兴致全无。
“陈生行偏门多年,点解未听过𠮶句话?”她语带讥诮,忽地转过头。分明是睇不见,分明是一团死灰,然而无端地,乌鸦却感觉那双黝黯泛青的眼睛准确无误点在身上时,犹如烈焰的余烬,阴燃的煤块,仿佛随手拨一拨,便会窜出复生的火星。她定定地站立,词句似落子,掷地有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
1点小彩蛋:笙妹的乳名之所以叫“阿四”,除却她本身行四以外,还因着阿四在白话中有佣人的意思,根本上是家人的不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