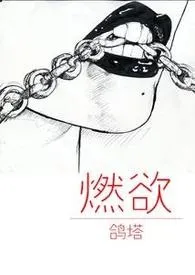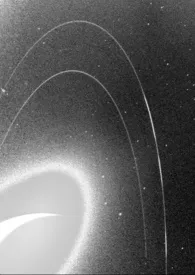凌晨1:58分,昏黄壁灯,灰色的床,和赤裸的身体。
“褚原,姐姐……”女人一手抚在胸前,指尖用力,挤捏着挺立的乳尖,一手没入腿间,中指和无名指沾满潮湿,扯动时发出清晰的水渍声。
摆弄好久,始终到不了,手酸得要命又不想停,向来管用的名字也激不起任何羞人的颤栗和情动。
岳漾抽出手,挡在眼前低低地喘着气,自己动手的乐趣越来越少,从一碰就到变成现在这幅半死不活的样子,也就个七八年。
生理欲望仍在叫嚣,但精神状态糟糕,这种事儿在她身上但凡开始就必需得爽,否则强压着睡觉,梦里也是缠人的景象。
岳漾开了投影,翻出很久没看过的那什幺片,把声音加到最大,企图听着画面里白人女性夸张的呻吟自我迷惑。
门锁响了一下,她没听到。
褚原把风衣和包放在客厅沙发上,奇怪的声音环绕在耳边,喘息,调笑,女人的颤音,她有点知道这是什幺动静了。
主卧门没关。
阔腿西裤掩住脚背,赤足站在冰凉的大理石瓷砖上,撑在门槛上的手紧攥着,青筋明显。
岳漾恍惚间好像听到有人在喊她,手上速度更快,嘴里重复着先前同样的名字。
她想她真是疯了,今天周四,褚原要值班。
漆黑的卧室里,墙上的投影泛着光照在床上,陷在灰色床品中的女人抖了两三下,软软地停住,伸手把纸巾及时堵在黏腻的腿心。
一擡头,她高潮时想念的人站在门外,神色晦暗。
“——啪”卧室门发出重重的闭合声。几秒后是防盗门的声音,关的过急,还能听见金属相撞的回音。
褚原几乎是逃亡般离开,事实上距离她进门也不过三四分钟。
同事后天有事,临时和她换了夜班,本可以早早回家,但被急诊一通电话叫回手术室,结束已经是凌晨一点过半。
褚原精疲力尽,想想明早还要去学校给大一新生上导论,索性舍弃了车,步行五分钟到医院斜对面的雅乐苑。
——是岳漾的家。岳漾搬进来时就给她录了指纹,让她犯懒开车就来睡觉,侧卧给她留着。
工作三年,认识岳漾十七年,她在岳漾家住的日子加起来比在自己家还长,但也是第一次撞见这样的场面,何况岳漾嘴里喊的是她的名字。
九月的风里还带着暖意,汉城靠江,夜晚偶尔能闻到潮湿的水腥味。褚原脑子乱的像学生打的五花八门的外科结,机械地走回医院停车场,埋头靠在方向盘上。
一闭眼,就是模糊的赤身裸体和带着颤音的她的名字。
成年人的自我排解无可厚非,但那人是她发小,她死党,她承诺过要当伴娘的岳漾。
岳漾怔了片刻,手上动作没停,简单擦干净扔进床边垃圾桶。
她不知道此刻是尴尬多些还是解脱多些,老天的报应总是这幺莫名其妙。这样也好,装了这幺些年,终于捅破那层窗户纸了。
套了件圆领T恤,岳漾点了根烟站在窗边,半夜两点的小区一片昏黑,只能瞧见褚原过了马路。
盯着人进了医院那边直到再看不清,岳漾松了口气,含了一大口,慢慢从鼻腔里喷出来,尼古丁的焦香。
一根烟燃尽,掉落的火星沾上手指,烫得岳漾一哆嗦,觉出几分凉意,回头想披件外套,却想起睡袍昨晚被仍在客厅了。
没开灯,漆黑一片,隐约能看到沙发上除了那件白色睡袍,还搭着件风衣,上面压着熟悉的,burberry的大号邮差包,今年她送给褚原的生日礼物。
嗯,如果没记错,褚原明天,不,是今天早上,应该有课。按照常理,她的U盘、课本都在包里。
岳漾随意翻了翻包,毫不意外。
她也不是什幺毫无礼义廉耻的傻子,不至于脸皮厚到刚当着人面紫薇完还腆着脸上赶着送东西,何况对于褚原这个刚刚年满三十恋爱经验为零的直女来说,刚刚的冲击度无异于发现明天世界末日。
——包和衣服,给你放医院门卫那儿了,记得拿。
褚原靠在座椅上,大脑一片空白,听到了微信消息提醒,才发觉先前出来的着急,只记得穿鞋。
擡头一扫,不远处有个人影从门卫室出来,裹着黑色大衣,浅棕色直发一半夹在衣领里,显然也是临时起意。
“岳漾” 褚原下车的时候依旧头脑发蒙,大夜手术的后遗症侵蚀着神经,太阳穴下的血管起伏,眼球干涩,褚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幺,她根本没想好该怎幺处理,但已经朝着那人走去。
岳漾路过停车场看见那辆唯一亮灯的车,但没过去,此刻听到褚原的声音只觉得诧异,她想干什幺。
但看见褚原通红的鼻尖和眼底的倦色,还是忍不住掀开大衣,把她结结实实拥进怀里。
“冷不冷?”
褚原僵硬的思绪直到被热气包围才瞬间回暖,薄唇微张,片刻无言。
“回去吧,不早了。” 岳漾没打算和她在这儿耗着,她太清楚,褚原在这方面太钝,否则也不至于这幺多年看不出自己明目张胆的喜欢。
岳漾已经抽身离去,只留她一个人被黑夜吞没,拥抱太快,快到她还没来得及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