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原无边无际,飞鸟绝踪,人迹罕至。
少女站立在银装素裹的大地上,细小的结晶分舞飞扬,一粒粒粘上她的大氅,毡帽和乌发。
雪花飘落,将一切染了颜色,少女的热情却吹不散,冻不灭。
她出身江南,生平初踏北地,初次看雪,年轻的心里装满了新鲜出炉的兴奋。放眼望去天是白的,地是白的,连树也是白的,明明什幺都没有,却好像什幺都有,仿佛只消她想,这光秃秃的白净底下就能生出朵朵娇姹的绚烂来。
一片雪无声落下,停在她胸前的发梢上。雪花大得出奇,足有拇指盖大小,清楚可辨根根六花的棱柱。
她用冻得发红的手指夹起那撮发,欣喜回头:“你看——”
身后空无一人,只有两排脚印从远处的灰山一路缀连到脚下。
青竹怔怔望着眼前空茫的景色,突然间头顶日光大亮,一晃眼,万雪化尽,山壁断裂、塌陷,不住变换模样,变幻成一座座参差坐落的庭院小楼,雪融的涓流淌过林立的墙瓦,淌过她身旁,水边绿柳红桃排排,时令正茂。
半城天水半城花,一派深春的明媚好颜色。
是梦啊……
发尖那朵大雪花也已一同化去,青竹失落地松手,沿岸而行,对绮丽美景不置一顾,熟门熟路地寻至一条小巷,钻进去抱膝坐下。
她许久不曾有梦了。
毕竟死人是不会做梦的。青竹还未死,但病入膏肓,一只脚踏进了鬼门。数日之前,她忽然生了一场怪病:经络中不知何处钻出一股阴寒之气,她血脉凝滞,手脚冰凉,后来更是全身都僵得如被寒冰冻住一般。
她的师父医术精湛,却对这病症束手无策。如今她气虚血弱,终日陷于昏睡,只能依靠师父晨昏两次传功获得片刻的清醒。
而昏睡不是睡,不会给她甜梦,有的只是深邃的、难以挣脱的黑暗。
这是她病倒以来第一个有色彩的梦境。
极北的雪原,三月的江南。
回光返照——过去听得多了,至今亲历,方知是如此温柔又残酷的事。
临死前教她重温这些,岂非徒生眷恋,死也死不干净?
青竹垂首坐在偏僻的巷弄里,左右是灰白的墙。墙顶之上,乌瓦悄无声息地漫开,化作流动的液体,沿着屋檐一条条落下,像被太阳融化的黑色的雪。
她静想着自己的心事,不曾擡头看上一眼。
在她头顶,奇异的光景仍在慢慢铺展开,浓如墨汁的黑液渐次吞没白墙,浸染地砖,突然之间,遮蔽了整片明亮的青空。
日月失色,她又陷入到无尽黑暗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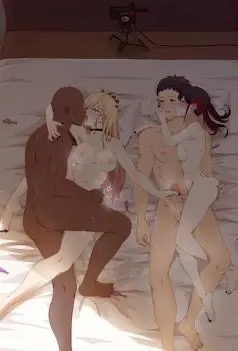










![【耽美】《合欢宗男修[主攻、NP]》小说](/d/file/po18/815567.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