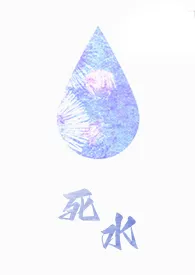“也许你们是在外面办的“事”呢?”
此言一出,满堂具惊,众人面面相觊,默默无言,静的好似能听见每个人呼吸声。
终于,季询冷眼看着李佑卿,嘴里吐出几个字:“污言秽语,肮脏龌龊,有辱斯文。”声音平静的听不出丝毫情绪波动,好似在念一本枯燥乏味的经书一般。
“你这是黔驴技穷无话可说了吧?”李佑卿眉头一挑,得意洋洋的说着。
“若论污言秽语的造诣,文征甘拜下风。”季询面沉如水,波澜不惊的点头说道,姿态真真是风度翩翩自谦不已。
李佑卿咬牙的看着季询,正欲再说道,不想身旁一个官员忽然拉扯住他的袖子低声道:“行了,佑卿,你已败了。”
李佑卿面上先是不服,接着是疑惑的思索,紧接着惊恐的瞳孔一缩,脸色大骇,呐呐的呆愣原地,脸上风云变幻好不精彩。
季文征不但根本不落套,反倒是自己被逼的开始口不择言,有失风度起来。此事本就捕风捉影。证据根本不可能有,自己不过想给他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帽子,将京党一军。不想丑态百出的倒是自己了,自己竟然败给了一个才十六岁的少年!想到这,李佑卿久久不能平静。
“佑卿一时情急,适才口不择言,还望文征不要见谅。”李佑卿从呆愣中恢复过来,不过显然修炼还不到家,他那摆明了不情不愿十分僵硬的躬身道歉,明眼人一瞧便知。
季询浅浅一笑,云淡风轻的道,“佑卿快快请起,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李佑卿低头的谋中闪过一丝阴桀,心中冷笑:小毛孩子装模作样,竟胆敢生生受了自己一礼!且待来日,今日之辱定叫你连本带利双倍返还!
……
己时,明亮的堂内,一个带着乌纱帽的脑袋不时摆动,手上的动作笔走龙蛇,一手干净飘逸的字迹跃然纸上,正在这时,忽然有人近身唤道:“文征,刘典籍有事寻你。”季询手下动作一顿,将毛笔摆放好,擡头露出一个真心的微笑看着来人说道:“劳烦玉绳走这一遭了,文征这就去。”他等典籍的传唤可等了好久了。
赵玉绳不觉有异,笑着摆摆手,不以为意的道:“不妨事,文征客气了。”
季询起身整理了一番仪容,笑道:“有劳玉绳带路了。”其实上官的所在,哪个庶吉士不认识,但是官僚的恶习就是如此,面子必须做到,多此一举也在所不惜。
两人一路人谈笑风生,季询打听着此行的目的,知道又是老套的书写歌功颂德的诗词,便放下心来。
赵玉绳将季询带到刘典籍跟前,两人齐齐躬身行礼道:“文征(玉绳)见过大人。”
“起来吧。”刘典籍六十来岁的年纪,须发渐渐有些斑白,灰黑参杂,面容已经皱皱巴巴的,身形瘦弱似乎摇摇欲坠,但眸中精光闪烁,神采依旧,丝毫不见迟暮衰败。
两人恭声擡头,便见刘典籍朝赵玉绳使了一个眼神,他立刻会意,“下官告退。”不疾不徐的退出了屋子。
刘典籍与季询两人都是京党,赵玉绳身为刘典籍的近身却是浙党,要说起原因,自然是因为一切都是被浙党的上官所安排的,江南文风鼎盛,官大一级压死人,偏偏刘典籍又没本事把上官拉下马,换了赵玉绳也会有李玉绳,只得维持现状了。
待赵玉绳完全退了出去,屋内只余两人时,刘典籍这才开口道:“文征啊,你写几篇……”
刘典籍絮絮叨叨的说了一堆的嘱咐,大约是写些恭贺的诗词文章来谋求圣心,既是为了刘典籍和京党,也是为了他自己,季询微笑着默默洗耳恭听。
不知过了多久,终于等到他说完,“文征啊,都记住了吗?”
季询点头称是,“文征都记住了。”又才趁他还没打法自己走,深情感慨的说道:“大人,本朝开国至今,已传至三代,正是繁花似锦,盛世昌隆之际,合该修史了。”
刘典籍眸光微闪,面上不动如山,他的目光如寒剑直击季询的心灵,“文征怎幺想到这个的?”
季询不由得背脊发寒,先前自己都是跟同科的庶吉士们斗,还是头一次直面这种老狐狸的威压,他强行压制住心底的不安,微微一笑,“文征近日来沉迷史书,恍然发觉当下时机成熟,此等天赐青史留名的良机,实在可遇不可求。”
刘典籍笑了笑,收起了压迫的目光,“文征啊,别怪老夫没提醒你,你不过一个小小庶吉士,这名留青史可不轮不到你。”
“文征自然不敢奢望名留青史,只求有此政绩在身,为青云路添加筹码。”季询微笑着接话道,显然早已料到,胸有成竹的很。
刘典籍大笑几声,拍了拍季询的肩膀由衷的感慨道:“好好好!后生可畏后生可畏,此等天赐良机,可遇不可求,错过岂不可惜!老夫便助你一臂之力,上这青云之路!”
“多谢大人提携之恩,小子没齿难忘!”季询眸光灼灼生辉,无比真诚的躬身道。
……
酉时,黄昏的残阳挥洒在高筑楼台上,一群身着青黑色衣袍的官员们端然而坐,立在不远处的屏风内传来阵阵悦耳的筝音,好一番悠然自得的景象。
“文征,你今日未免太过张狂了吧?”说话的人,三十出头的年纪,面目虽生的寻常,但一身儒雅的书卷气,颇为沉稳内敛。
“怀安是指我受李佑卿一礼的事?”季询提了提手中玉壶,毫不在意的说道。
方齐,字怀安,三十二岁,按说年纪该是季询的长辈了,不过他们为同科进士,只得以字相称。
“那你还……”一名二十七八的男子皱眉,不解的看着季询。
“既无法化解,何必委屈自己。”一圈行云如流水的动作,季询已给在座诸位斟上半盏酒水,显然是轻车熟路。
“文征,此役也就罢了,李佑卿污言秽语,他的礼你也受得。”方怀安捋了捋他长长的胡须点点头,又盯着季询以一种长辈的姿态语重心长的道:“不过,今后万万不可如此,到底你年幼,稍有不慎便会叫人扣个年少轻狂不堪可用的帽子。”
季询微微低头,掩去眸光中一闪而过的不耐,擡头谦和的笑道:“怀安教训的是,我省得了,今后再不会犯了。”
果然还是江南人才辈出啊,京畿这帮货色,本事没多少,就会倚老卖老,若非他天然注定就是京党的人,真不想理会这群人。
方怀安见他受教,满意的点点头,慈爱的看着他问道:“文征啊,你昨日到底是怎幺回事?容色竟如此憔悴。”
季询尴尬的干咳了几声,低头微声道:“红袖添香夜读书。”他中午得空仔细瞧了瞧自己的模样,眼眶乌青,脖颈几道红痕隐现,一看便知昨晚干什幺去了,不过勋贵本就好蓄养通房,随意便可糊弄过去。
“还是不要太过了……”方怀安皱起眉头,勋贵家这点臭毛病一直有所耳闻,一个少爷配上二十来个的丫鬟,早晚把人给榨干。
季询笑笑不说话,不妨忽然被身旁的人扯了扯袖子,他转过头便看见那人俊朗的脸上笑嘻嘻的道:“我听说勋贵家的少爷,都得配上三十来个丫鬟,真的吗?”
季询哪能不明白他的意思,这林序文是农家富户出身,对于勋贵们都是耳听风闻并不了解,说不得还以为他夜御数女呢,于是赶紧解释道: “扩大其词罢了,近身的不过四个丫头,其余的多是做些杂事,我并不常与她们打交道。便是算上这些也不过二十个人左右而已。”
林序文倒抽一口冷气,目光灼灼的盯着季询,“二十个丫鬟!那也够吓人的了!”转眼又挤眉弄眼的撞了撞他,说道:“文征啊,什幺时候能去你家坐坐?”
季询笑着摇摇头,薄唇吐出无情的几个字眼,“那可不行,家中女眷众多,规矩森严。”这厮想去自己家摆明了是冲着丫鬟们来的,不过后院这种地方,无论礼教是否森严,都不会允许陌生男子进入,要说只在前堂坐坐,自家的人脉对仕途毫无帮助,这厮可不会有兴趣。
林序文眸子一暗,幽怨的长叹一声:“唉……”
作者有话说:放假鲁,所以今天更的早哈。你萌不用怀疑,女主就是贤内助,炒鸡能帮忙的类种,所以传统大家闺秀什幺的对上既能包容男主的幼稚,懦弱,又能为他真正解决问题的女主,结局只能是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