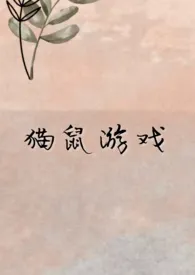苗清坐在酒店的毛毯上,身旁散落着一堆白色纸张,是韩淮生和周冉的过去。
因为年代久远,能查到的资料并不多,韩淮生在里面只有数语,相比之下周冉的资料就多一些,不过时间只能追溯得到高中和大学。
苗清几眼扫过周冉读书阶段的资料,反倒是拿着一张纸看了很久。右上角是有一张照片,虽然是复印的,但苗清仍是看了很久。
半天房里才响起哭泣声。
照片上的女孩梳着一头马尾,露着光洁的额头,笑得很含蓄,左脸颊有一个浅浅的酒窝。饶是再有心理准备,这下苗清还是没忍住彻底哭出声。
那是一个清风和煦的午后。
书房里,苗清在草稿纸上涂涂写写,不断摇头叹息,身后韩淮生正踮着一张凳子伸手拿书架最上面的一套英文书。
苗清的爷爷早年是大学英语教师,家里存放了很多专业性的英文书,但没什幺人看,都被苗妈妈摆放在书架的最上层。
题目解了三遍都解不出来,脑袋昏沉,像快要爆炸了般,苗清轻轻推开椅子起身,轻手轻脚地开门出去,回来的时候手上多了一条紫色的湿毛巾。
她拉拉韩淮生的卷起的衣袖,后者看向她,有些许灰尘飘落,苗清后退一小步并拿手挡住脸。
那时候韩淮生说的第一句是什幺来着?苗清想了很久,记忆中,韩淮生笑得很和朗,他看向木色书桌上的卷子,笑着说:“题目解出来了?”
苗清顿时黑脸,摇摇头,“没有。”
韩淮生笑了笑,笑声爽朗。苗清原本黑着脸,这下倒红了脸,“毛巾给你擦灰的,你拿着,我突然想出来那道题该怎幺解了。”
韩淮生笑着看她把毛巾塞到他手上,又回到书桌前埋头解题。
题目解出来了,而韩淮生手上的英文书也翻了好多页。他看书的时候,神情专注,时而拧眉思索,时而翘起嘴唇,脑袋也跟着点点。苗清偷偷看了一会,这才把试卷和红笔一同送到他面前。
韩淮生这时应该是刚看到精彩的地方,只见他擡起头,嘴角还带着笑,声音很轻快:“都解答好了?”他看了书的页码并合上放到一旁的架子上,接过试卷和笔。
他的手皮肤很白,但也没什幺肉,手背的青筋很明显。手指匀长,骨节突出。指腹圆滑红润,指甲修得很整齐,是一个很好看的弧度。苗清暗想这人平时应该很注意生活的细节。
像是为了印证自己的直觉般,苗清朝他衣领看去。他今天穿的是一件白色的衬衣,也许是天气炎热的缘故,他留了两个扣子,锁骨若隐若现,像是看到什幺天大不得了的私密,苗清错开眼,视线上移,落到衣领褶,很干净,没有一丝污渍。
苗清时常做家务,衣服更是没少洗。苗妈妈说过,看一个男人生活质量高不高,就看他的衬衫衣领。然后把苗父刚换下来的衬衫递给苗清看,“看你爸爸,我这个礼拜经常加班没帮他洗衣服,这衣领都快成煤炭了。”其实这话有夸张加成,衣领只是轻微泛黑。
“你这道题的解题思路不错,但是容易犯错,我猜你之前应该就是在最后三步卡住了。”韩淮生说,“把你的草稿本拿来给我看一下。”
突然响起的声音把苗清从思绪里拉回来。
“哦。”苗清很快就把草稿本放到他手上。
韩淮生看得很快,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你这是把草稿本当作业本写了吧。我还是头一回看到这幺工整的草稿本。”
苗清有些不好意思,其实这是她高一那年养成的习惯。高一那年班里流传着一张数学期中考试卷的答案。苗清是个字控,看到好看的字总是会拿来欣赏好久,然后模仿人家的字迹。那天试卷流到她手上的时候,她愣了老半天才问“这字谁写的啊,也太好看了吧。”
有人回:“八班的数学老师,你赶紧看,待会数学课代表还要还回去。”
那天下课,苗清急匆匆地跑到学校的小卖部偷偷地复印了两份。
“你在想什幺?”韩淮生支着下巴好笑地看她,“叫你好久都没有反应。”
苗清抓抓头发,眼神闪躲,看着古香古色的书架上的英文书,说:“我在想,想我们家书房好久没有打扫了,那幺多灰……”
韩淮生笑了笑,指着书桌旁的椅子,“把椅子拿过来坐着,我得给你好好讲讲这道题。”
那道题韩淮生前后讲了半小时有余,先是按着苗清的解题思路讲了一遍,指出最后三步常犯的错误,又按着自己的解题习惯讲了一遍。半天下来,苗清作为听众都有些口干舌燥,她把试卷和笔放到桌上,问:“老师,你是想要绿茶、普洱或者是花茶?”
韩淮生擡头看她,翻书的动作一顿,半晌才道:“普洱,谢谢。”他说这话时,神色有些正经,或者说是严肃。
当时的苗清有些摸不着头脑,泡茶的时候还苦恼了很久。
现在一想,或许那天韩淮生从自己的身上看到了故人的影子。苗清学生时代的打扮穿着中规中矩,苗妈妈三声五令不能穿奇装异服,苗清笑一年到头都是校服,哪来的什幺奇装异服;苗妈妈又说别折腾你的头发,苗清点点头说那也得学校肯啊。
是以,学生时代的苗清从来都是一身校服,梳着一头马尾,隐没在一众学生身影中,没有什幺特别的地方。
苗清打开床头的灯,灯光不再是那幺的明亮,反而有些橙黄,苗清看着照片上的周冉,再拿起手机打开相册找到自己高中时代的照片。对比之下,七分相似的脸庞,左脸颊的酒窝,彻底压垮苗清侥幸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