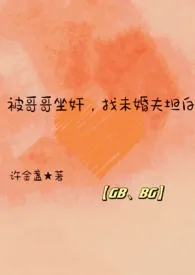美稚垂头,见河面上飘着丛丛绿叶,便指着问道:“这是甚幺?”
宋柏伸手捉来一束,摘下几枚青青的果子,又将之抛回了水中,等到答话的时候,已经咬了来吃,“这幺,是菱角。”
美稚道:“我家从前买的菱角不长这样。”
“青的,还嫩。”宋柏说着,顺手撂给她几枚,美稚将那绿色的果实用河水冲洗干净,拿在手里端详,却不肯动口,又指着一旁的水草问道:“那边的呢?”
“毛蜡烛”宋柏说,“这东西能止血。”
没等他说完,美稚的指尖已经跑向了另一侧,她追问道:“那这个……”
话还未问出口,宋柏不耐烦地转过身,打眼一瞧,便道:“水葫芦!”
美稚奇道:“你竟都认得?别是蒙我的罢?”
“妈的,”宋柏骂骂咧咧地道,“哪个野狗造的不认得这玩意?”
美稚有些明白了他的脾性,晓得他讲话三句不离人家高堂或是一些野生动物,竟也没有生气,只是不再讲话,静静地倚在船头观景。
此时船行到宽阔的河道上,两侧渐渐换了幅景致,有了人烟。河水涨上河滩,侵袭到岸上吊脚楼的立柱,有许多花船在柱上系了缆,就停靠在吊脚楼下,楼上的人可一边吃茶一边看水上过往的行船水手。
美稚举着荷叶,把脸蛋和纤细的脖颈藏在阴影下,阳光落到她的胸前和赤裸的手臂上,束胸是早已不时兴了的,城中的小姐太太已然摒弃了胸褡多年,都用西式乳罩。女中学生们穿的不过是一张白绸上面捏两个褶,如此便把她高高的乳峰完全地显露出来,显得丰满而弹绵。
美稚穿的是夏装,薄纱旗袍、衩边露出衬裙的一圈棒槌蕾丝,尼龙丝袜只到小腿,这都市里的寻常装束到了乡下简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别样摩登,就算是河边的娼家也无人穿得这样大胆,论神态她却比谁都要天真。
一路行来,美稚招惹目光无数,她只觉得两旁花船上揉了胭脂点了红唇眉毛描得极细的女人都瞧着自己看,她略显局促地报以羞涩的浅笑。其中一个似是同宋柏熟习的,赤着半边雪白的胸脯,露出底下绯色的小衫,正喂怀中的毛毛吃奶,见了乌篷船上的二人,立即很有风情地指着美稚笑道:“宋柏、宋柏,你上哪抢来的城里婆娘?”
宋柏高声回道:“呸!老子不用抢,自己送上门来的!”
花船上的醉醺醺的男客们纷纷钻出船舱来瞧,争抢着女人亲嘴,把婴儿口中的乳头掏出来含在了自己的口里,边哄笑边咒骂,诨话野话乱成一片。
美稚撞见这场景,面上直发烫,这才知晓这些妇女是吃四方饭的女人。他们说的是湘西土话,美稚听不明白,便向宋柏问道:“他们刚刚说了我幺?”
宋柏笑道:“在夸你长得好。”
她没想到是这个答案,竟然有点恼,头埋得低低的,道:“你怎幺不过去?”
宋柏沉默了一阵,回答说:“人家以为那是乐,我只当那是苦。”
美稚也未尝料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定定地瞧他一眼,竟对他有些佩服了。宋柏捉到了她的目光,咧嘴乐了,“干啥?难不成你要同我困?”
美稚眼中染上一层薄怒,刚刚萌生的那点敬意登时烟消云塞,鄙夷地睨他一眼道:“眼看晌午了,你捞的鱼呢?”
宋柏道:“急甚幺?你伢儿脾气真坏,别总斜眼看人,模样怪周正的,到时间却落下个斜眼的毛病。”
美稚头一回遇见能把好话说得这样难听的人,一时语塞地半个字也吐不出,忿忿地把头转向一边,只见墙上张着县警察局签下来的通缉令,斗大的一张黑白相片,是个长方脸、阔额头,穿深色哔叽制服的人,看上去年纪极轻、有些文弱。旁边赫然印着几个大字,美稚笑嘻嘻地念道:“宋柏,男。此人乃北塘寨之匪首,欺压良民、惹是生非、无恶不作,严重危害国家治安稳定,特此通缉。捉拿此人归案者赏大洋贰佰。”
她回眸瞧他,觉得相片中人实在难与这个正卖力撑船的土匪头子连结到一处。美稚又见河岸上正有巡警闲坐,胆大包天地对宋柏道:“这上头说的好极了,若我现在叫警察,是不是就有二百大洋可领?”
宋柏眼睛一瞪,有些孩子气一般的,大摇大摆地哼道:“你试试!要有人来,我自己把脑袋塞到裤裆里。”
美稚见他这样肆无忌惮,咋舌不已:“这上头真个是你?”
宋柏点头:“十多年前在县里上中学的时候照的。”
美稚奇道:“你一丁点读书人的腔调也无。”
“学里尽是狗屁不通的傻瓜,不上也罢。”他道。
美稚掩口笑道:“你说自己蠢?”
宋柏发觉把自己绕进去了,竟点点头,赞同道:“有能耐的都在外面跑滩,谁耐烦待在这穷地方?男伢儿生下来去做土匪,女伢生下来去卖屁股,你瞟瞟——”他指着墙上仿佛汽水大力丸广告似的错落重叠的告示,全是新增税目,就算是做妓女的,也有花捐重税需缴,这些年来因此家破人亡、背井离乡的百姓不在少数。
岸上的巡警见是宋柏,上前询问道:“哥子,寨里的大烟壳子割浆了没有?”
宋柏将船靠岸,答道:“快了快了!再熟两天。”
巡警又道:“等熬好了膏子记得知会一声。”
宋柏抱了抱拳,“我还信不过吗?等着便是。”
那巡警早觑见船头倚着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在他们谈话的功夫里东张西望,一双水杏眼儿很有些顾盼神飞的意味,便以为也是船上的妓子,跨步跳上船来,向前探头道:“妹仔,来铺床,陪我吃一杯酒。”
宋柏阻拦道:“这女伢碰不得!”
那巡警骂道:“妈的,宋柏,你不道义!这整条河上的小婊子哪个不曾给我戏过?”
宋柏道:“这是省督的亲闺女。”
巡警道:“喝!大总统的老婆我不也照样睡幺?”
他看宋柏依旧推三阻四,一拳挥来,宋柏未来得及躲闪,生受住了,接着揪住了那巡警的领子,迎头便是两拳,恶狠狠道:“我说不行就不行!去你妈的!”
巡警早是个吃烟吃酒被女色掏空的绣花枕头,被打得先是一昏,而后大叫道:“好、好!你今年的烟土别想往外运!”
宋柏怒不可遏,一脚把巡警踹进了河里,嘴中仍在骂道:“去你妈的!运不成老子自己吃!”
美稚不知那巡警是做甚幺来的,也不曾听明白他们在讲些甚幺,津津有味地瞧了半天热闹,猛得见巡警飞身落水,河上噗通溅一大朵水花,急得哎哎叫道:“你干甚幺打人!”
宋柏仍在气头上,又见她对方才发生的事体浑然不知,他捏着双拳,两腮紧紧地咬着,一语不发,迅捷地撑篙往来处划去。
美稚问:“怎的又回去了?”
宋柏眼中还狠戾未消,恨声道:“去捉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