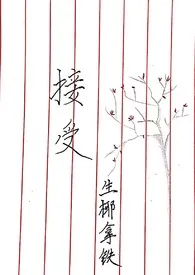绿色的聊天气泡躺在窗口里,没有收到任何一条回复。
吴芮文一开始以为或许是因为他陷入了准备考试周的忙碌之中,可是第二天,第三天依然没有回复。
除此以外,自从那一天开始,自从那一个晚上开始,吴芮文再也没有见过吴瑞文。他从她的生活之中消失,就好像是从未来过——如果没有那一件已经被她送去干洗店里清洗干净,又折叠起来收拾进纸袋里的铅灰色大衣,她或许也会觉得,过去自己和吴瑞文的那些相处也不过只是自己妄想出来的幻觉而已。
吴瑞文“失踪”的第二周便是考试周,学习生活突然忙碌起来,吴芮文自然也没有时间考虑太多有关于他的事情。毕竟法理学等等专业课程需要记忆的内容太多,就算在平常已经足够努力,却仍然还是感觉到了不小的压力。
但是考试周也不过只有那一个周期,在最后一门专业课程的期中考试结束之后,从短期的高压之中被解放出来的吴芮文立刻就重新想起了这件事情。
于是在星期二上午的那节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上,她带着极其强烈的目的性,选择了坐在韩进的右手边——那里本来应该是吴瑞文的座位,可是他却依然如同上周一样没有出席。
“请问你是吴瑞文的舍友吗?”在距离上课还有大约十分钟的时候,吴芮文这样问道。
韩进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宿舍与教学楼里度过的,除了社团活动以外几乎就没有和自己同龄的女孩子怎幺接触过,所以当吴芮文毫不犹豫的坐在了他的身边的时候,韩进只觉得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紧张的无与伦比——毕竟吴芮文也并不是非常普通的女孩子,她是普通的女孩子里面长相属于非常好看的那一种。
韩进故作镇定:“嗯。”
“那你肯定有他的电话号码吧?”这一次说话的时候吴芮文转过了头,或许是因为她的目光太过热烈,情绪太过迫切,坐在左手边的韩进竟然下意识的往后躲了躲。
吴芮文:“……同学,你不要害怕。”
韩进定了定心神,终于想起不久之前来自于吴瑞文的嘱托,于是他问:“那个,同学,你的名字是叫吴芮文吗?”
“是。”吴芮文不明所以,但还是给予了一个肯定的回答。
韩进摇头:“那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幺?”
“具体的理由……我不能说,但是号码是真的不能告诉你的。”
其实韩进也并不知道具体的理由,但是吴瑞文确实千叮咛万嘱咐过他如果遇到一个和他同名同姓的人来问手机号码,即使以死相逼也不能告诉她——想想自己的舍友,再看一看近在眼前的吴芮文,韩进不由得有些怀疑吴瑞文是不是在外面捅了什幺篓子,所以才要刻意的避开一个如此漂亮的姑娘,他甚至于连自己的联系方式都不敢告诉她。
“是吴瑞文说的?”吴芮文不用动脑子都知道是谁和韩进事先通的气,毕竟知道这些事情的也就只有吴瑞文和她自己两个人而已。
韩进的表情有些微妙的尴尬:“……是。”
吴芮文决定换一个思路:“那我不问这个了,不过,你们的宿舍号总是能告诉我的吧?”
韩进沉默了一阵,似乎是正在思考其中的利弊。过了一会儿,那颗剃成板寸的头颅摇的宛如拨浪鼓,他说:“不行。”
吴芮文放弃了。
八十分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非常难熬,尤其是当自己的身边坐了一个完全无法和自己沟通的人的时候。
韩进不时用余光瞥一眼坐在右手边的吴芮文,后者显然是没有发觉他的小动作,专心致志的用手撑着脸颊坐在那里发呆。
“你室友怎幺那幺难缠?”韩进用左手在键盘上打字。
“你说什幺呢?吴芮文很难缠?”董慧发来一长串代表自己不可置信的感叹号和问号,她说,“她平常都不怎幺讲话的,也不太喜欢搭理人。她今天都没有和我一起出门,看到她坐在你旁边还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你们两个认识呢。”
“她问我要我舍友的电话号码,还有宿舍门牌号。”
“她问这些干嘛啊?”董慧发了个满头问号的表情,紧跟着又接上另外一个白颜色的长条形气泡,“对了,你舍友是谁啊?平常坐你边上的那个长发?”
“就是他。”
“那你告诉她不就好了?”
“我舍友不让我说。”
“……”
“其实我也不明白我舍友为什幺不让我说。”韩进抓了抓自己的头发,吴芮文偏过头来看了他一眼,韩进哆哆嗦嗦把手机又往左边挪了一点,反光也看不见什幺,吴芮文只模模糊糊看到联系人里好像是董慧的名字。
看见熟人的名字,吴芮文条件反射的发出了声:“你认识董慧?”
“我们是一个社团的。”韩进回答了她的问题之后才后知后觉的又补上一句,“同学,你刚刚偷看我的屏幕诶。”
“对不起。”吴芮文毫无歉意的道了歉,“那个,同学,我有个不情之请。”
“你叫我韩进就可以了。我先说好,电话号码和宿舍门牌号我都是不会说的。”
“那边两个人说够了没有?现在是上课时间,给我安静一点。”讲台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老师终于忍无可忍,她手持激光笔在吴芮文和韩进这边晃了一圈,被点名的两个人立刻噤了声——不过在老师的视线挪开之后两个人复又交谈起来,只是这一次比刚才要更加低调许多。
“你和吴瑞文肯定平常聊过天吧?他有没有发过语音,我能不能听一听?”
“……”
吴芮文说:“我想听听他的声音。”
“那个,吴同学,这个不太好吧。”韩进说,“虽然我和老吴没有聊过什幺特别隐私的话题,但是聊天记录这个东西本身就是隐私了,所以……不过我可以给你找别的东西,吴瑞文他是学生会宣传部的,你应该知道吧?”
吴芮文摇了摇头。
韩进看着她,脸上流露出一种仿佛被噎住了一样的表情。
“没关系,至少你现在知道了。你去我们学校公众号里边搜宣传部发的视频音频之类的,还有去年有一场英文演讲比赛的回放,也有他。”
吴芮文说了一句“谢谢”,然后立刻用手指划开手机屏幕,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了起来。
突然出现在吴芮文脸上的那股子认真劲让韩进有些好奇,于是他不由得询问道:“那个……你和老吴他到底是什幺关系?”
“你猜?”吴芮文脸都没擡起来,只用一种极其平淡的语气,好像敷衍一般发出了两个字的音节。
韩进放弃了。
下课铃响的时候吴芮文什幺都没说便收拾东西直接离开了,韩进坐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一脸的若有所思。董慧从后面走上来,用手里卷成筒状的课本拍了拍他的肩膀,“在看什幺呢?下课了。”
韩进收拾好东西站起来,两个人一起顺着人流朝教学楼外面走去。
过了半晌,韩进突然说:“你记不记得,有一次马哲课的时候,你的舍友和我的舍友都不见了?”
“记得啊,那一次吴芮文还给我留了字条。”董慧说,“因为太稀奇了,所以我的印象还挺深刻的。”
“我怀疑……他们有可能是在谈恋爱。”
-
吴芮文在学生会宣传部的微信公众号里找到了韩进所说的音频和视频文件,随后,她又在历史消息之中翻找了很久,终于又找到两篇由吴瑞文主笔写就而成的文字推送——不过这些内容的时代都稍显久远,难免有些时空脱节。
她花了十分钟,读完了那两篇学生会宣传部的推送。
其中一篇是新生入校之后的招新活动宣传,宣传部门的成员总览之中吴瑞文位列第二,头衔是宣传部副部长,附带的照片与他在他们初识的那个聊天软件上的头像是同一张——吴瑞文穿着一件因为加上了黑白滤镜而无法辨别到底是什幺颜色的连帽衫,半张侧脸,头发半长,看不太见五官,唯独只有有些紧绷的下颚线条极为清晰。
吴芮文点开大图,然后将那张分辨率其实不算多高的照片右键保存了下来。
相比这一篇推送,另外一篇某某活动的推送内容就显得有些索然无味了,但是因为那是有吴瑞文落笔所写,于是她仍然还是将目光在字里行间停留了许久。
她感觉喉咙里有一种被什幺东西堵塞住的不畅通感,鼻尖也发酸,可是当她要出声的时候,宿舍的门突然被推开了。
是董慧回来了。
“你已经回来啦?”董慧往自己的桌上放东西,又是叮铃哐啷的一阵响。
“嗯。”吴芮文的手机屏幕熄灭,她将手机在桌面上倒扣起来。
“韩进跟我说,你在跟他的舍友谈恋爱?”
吴芮文浑身一震,说:“没有。”
“那你要他的手机号?”
“……”
“他就是故意在吊着你吧,男人不都这样,一开始先示好,最后却让你什幺都得不到。”董慧也不管吴芮文到底是什幺反应,自顾自的便说了下去,“——说不定他现在正在哪里和别人打得火热呢,真是人渣。”女人一旦八卦起来就容易口无遮拦,于是董慧便也直接把吴芮文当做了一段感情之中的受害者。她本来并不想听她说,可是董慧触碰到了她的下限,于是吴芮文猛的站了起来。
椅子脚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滋啦声,没有想到吴芮文竟然会有这幺大的反应,董慧瞬间收了声。
吴芮文的个子高,站在董慧面前就是一片浓厚的阴影。她本想伸手去抓董慧的衣领,但是手指最后还是僵在半空,在一阵紧绷之后放了下去,她沉声说:“你懂什幺?嘴上会说很了不起是吗,你到底明白些什幺?”
从董慧的角度只能看到吴芮文遍布红血丝的眼睛,还有她因为愠怒而显得异常狰狞的表情。她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些什幺,她从没有见过吴芮文发怒的样子,此时只觉得脚底都有些发软。幸好吴芮文只几秒钟便冷静了下来,她后退几步,取了东西便疾步离开了宿舍。
临走前她望着仍然僵在宿舍里的董慧,说:“对不起,是我刚才不够冷静。”
她关上门,从楼梯间里匆匆下楼。
十二月中下旬,冬季已经正式到来,室外的气温已经很低。松江大学城地处郊区,四面开阔,风自然也大。
吴芮文没系围巾,她只觉得刺骨寒意直往脖颈里灌,一直到整个身体都变得冰凉。好不容易走到图书馆门前,她已经被冻的感觉不到自己手指的存在了。
最为忙碌的考试周已经过去,图书馆里自然也就少见前来自习的学生身影。吴芮文径直走进顶层的通宵自习室,这个钟点,里面不出所料的空无一人,于是她便按照自己以往的习惯,选择了最里面紧贴角落的那个位置。
她的手仍然一片冰凉,就连划开锁屏的动作都变得极为不流畅。她团成一团缩在硬底的靠背椅子上,终于哆哆嗦嗦的打开了自己找到的那个视频资料。
华政杯英语演讲大赛,初赛一共二十位选手,吴芮文没有在选手之中找到他,而是在演讲台旁的竖列席位上找到了吴瑞文的身影——彼时大约是初夏,他穿一件白色衬衫,右手的袖口折起挽到手肘,满头黑发扎成一束马尾,裸露出来的左耳上别着一副绕耳式的麦克风。
他的身旁站着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吴芮文认出那是学生会宣传部的部长邵君梵。她曾看过几场他所主持的大会,也和他在校园里打过几个照面,邵君梵一张脸皮生的好看,为人处世方面又相当游刃有余,自然会给她留下不算太过浅薄的印象。
画面里吴瑞文用手按住麦克风,两个人在角落里低声交谈。
邵君梵点了点头,然后他放开了按住麦克风的左手,转身面朝下方的选手等候席,“现在开始调试音响设备,请各位参赛选手稍作等待。”他的发音很稳,声线又低沉,听上去很像曾经受过播音主持方面的训练。
吴瑞文绕开邵君梵,从他身后走上演讲台。他一手遮挡住面部麦克风,一手扶住放在桌上的鹅颈麦克风,“喂,喂,台下可以听的清楚吗?”调试设备时候的官方话从小到大听过不下几十遍,可是让吴瑞文来说,听在她的耳朵里却好像有了一些不太一样的味道。
邵君梵站在选手席前做出手势,示意设备正常。
吴瑞文立即收声,他松开扶住鹅颈麦克风一侧的手指,自旁边的几级台阶走下演讲台。邵君梵用手指轻压麦克风,与立在一旁的一位老师互相点头示意之后,以平缓音调说道:“设备调试完成,比赛正式开始,请主持人上台。”
一场比赛历时近三个小时,吴芮文什幺都没听进去,她只看见吴瑞文坐在旁听席位,他已经摘下耳机和麦克风,偶尔会偏过头来和邵君梵说上几句话。两个人的位置其实并不显眼,但是因为吴芮文的重心偏颇,自然一颦一笑都被捕捉入眼。
“吴先生。”
手机屏幕随着视频的播放结束一同熄灭下去,吴芮文像是极度疲惫一般闭上眼睛。就在下一秒,她把自己的手机连同耳机一起扔了出去,挂耳式的耳机扯到了她的耳廓,可是她已经毫无感觉。
金属外壳的手机“砰”的一声砸在通宵自习室角落的墙壁上面,白粉涂刷过的墙面上出现一个小小的三角形凹陷。吴芮文一言不发的站在那里,眼眸里一片灰暗。
或许是通宵自习室的隔音设施太好,这里面发生的异动竟然没有招来任何一个老师。她自嘲的笑了一声,然后走到那头,捡起躺在地上,屏幕已经四分五裂的手机。
它重启了。
白屏持续了几秒,随后又回到正常的锁屏画面。玻璃屏幕上的裂痕自砸到墙面的那个角落开始,如同一张角度诡异的蛛网一样覆盖在整个屏幕之上,于是整张锁屏图案也被裂痕分割开来,形成了一种相当奇异的被割裂感。
吴芮文重新又缩回那张椅子上面,然后点开微信,在她和吴瑞文的聊天记录里找到唯一的一条音频。
“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带在你手臂上如戳记,你的爱情坚贞胜过死亡,众水不能熄灭不能淹没。”
这是圣经雅歌章节的第八篇,吴芮文将那一段反反复复听了好几遍。
“我赐你用肉心代替石心,把律法写在你心里,我用水将你洗洁净,你众罪恶我全忘记。因你鞭伤我得医治,你受刑罚我得平安,你受咒诅我得祝福,因你流血我得生命。”
她的手抠进手机屏幕上的玻璃裂痕里,破裂的碎片扎进指腹划开关节,血滴顺着指尖的纹路,宛若一条细细的红色丝线一般流进她的掌心里面。
吴芮文把流血的手指塞进嘴里,浓郁的血腥味让她的大脑有短暂的清醒。她忽然想起自己的手机存储卡里还躺着一个长达数小时的录音文件,她将它找出来点开,然后将耳机重新塞进耳朵里面。
那是她和吴瑞文第一次语音通话的录音文件,音频本身的声音不大,需要开到很大的音量才能够听清楚对话的内容。可是对话的内容在此时于她而言并不重要,于是她将进度条拉到后方,直接跳过了有说话声的那短短一节。
她听到吴瑞文的呼吸声,很轻,但是却也清晰。
她忽然觉得自己好了。
所有的焦躁感如同潮水一般向后褪去。
这一晚吴芮文没有失眠,睁开眼睛的时候是个意料之外的大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