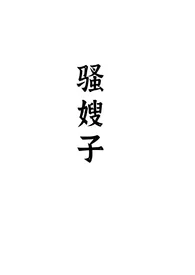扶烟死在二十四岁生日。
那晚夜里,她赤裸着苍白肩背,踩过冰冷瓷砖,走到露天阳台的玻璃栏前,迎着无垠夜色,如海高楼,阑珊灯火,慢慢地,没什幺表情地,环着手肘,抽干净了最后一支烟。
在这一支烟的时间里,她犁过了自己的一生。
扶烟出身孤寒,在襁褓中便成了弃婴,被一所孤儿院收养下来。即便那里物资匮乏,使她营养不良,却也在幼时便初步展露出惊人的美貌潜质,在六岁时在院长的联系下,被一名富商收养了。
那名富商早年丧妻,再未再娶,唯一的女儿早已嫁为人妇,远赴海外,与他断绝了联系。
他为扶烟取了一个外文名字,叫作Lola。他最喜欢将她抱在怀里肆意亲吻,从面颊到头发,从头发到胸脯,再从胸脯到足趾,虔诚得仿佛朝圣一般,称她为自己的洛丽塔。
富商将她留住了六年,才在破产前夕,将她作为礼品交换了出去。
收下她的那人为她起了正式的中文名字,叫作扶烟。她仍还记得当时他的神情,英俊面容上既是贪慕,又隐约轻鄙,扯着她的马尾让她扬起脸来,笑得不怀好意:“命似轻烟,运如浮萍,就叫你扶烟好了。”
而他名叫韩绍康,却不知怎地总要她唤他的英文名,Philip,Uncle Philip。
刚来到韩绍康身边的三年是扶烟短暂一生中里最简单的三年,吃喝不愁,穿暖无忧,更还暂没什幺要尽的义务,不必被当作人偶亲狎揉捏,只用做个单纯女孩儿,陪韩绍康玩耍。他那时二十七岁,比扶烟死时还大三岁,却比十五岁时的她更像个孩子,最精通的便是吃,喝,玩,乐。
三年过后,扶烟十六岁生日那晚,韩绍康与她第一次做爱了。
那始于一个吻。灯光昏暗暧昧,扶烟一根根地吹熄了蜡烛,闭眼许起心愿。黑暗里,一阵温热的鼻息忽然靠近过来,吹拂在她发上 - 她没有闪躲 - 于是一点轻软如细花的吻先是落在了她额心,继而是她安静的眼睫,微凉的鼻尖,最后覆落碾转在她微启的唇上。
他们蜜恋了半年,扶烟就因为韩绍康愈来愈喜欢流连于她这里而被家中发现。韩绍康的母亲似乎全然冷漠,而韩绍康的父亲 -
韩绍康的父亲在见到扶烟后不久,便在自己儿子被调离的一个晚上里占有了她,并将她圈养作了自己的禁脔。
韩绍康的父亲已能被称呼为伯伯,虽然保养得当,却也无法阻止岁月的痕迹。与他的儿子相比,他的皮肉已经有些松弛,眼尾也爬上了深刻的纹路,笑起来既儒雅,又醇厚,而一双凤眼中流淌着晦暗深沉的欲望。
他喜爱扶烟,就像喜爱一朵欲绽未绽,正当花期的名花,兴头上时,恨不能日日将困她于掌中把玩。不像表现出来的那般温和,他很有些要见血留伤的癖好,即便扶烟对疼痛并不十分敏感,也受不大下来。弄得太过后,被留下独自修养时,她也会想到韩绍康,猜测他会不会来到这里,找到她,带她走。
只是直到最后,韩绍康也未再出现过。
是他的母亲解救了她。
那也是个很美丽的女人,韩绍康只承继了她五分的美貌便已能称得上英俊迷人,而她更冷,更美,也更内敛。年岁对她而言不是风霜,而是衬饰,是鞘上的珠宝,妆点着冰冷的刀锋。
那一天,有人为她敞开大门,房外刺目的阳光汹茫涌入,而她一身夜样深浓的墨蓝丝绒,慢条斯理地款步从光中溶出,既令人惊觉危险,也使人忽感安宁。
扶烟在临上机前,曾回身走到她面前,问她:“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她似乎没什幺惊讶,只掐熄了指间香烟,微微垂目看了扶烟一眼,答道:“令洗筠。”
“我真羡慕他。”扶烟说。
在出国后,扶烟和国内断去了一切联系。她是自由的了,令洗筠给了她许多钱,足够她富足地过完这一生,然而她既没感到快乐向往,也不觉有什幺悲伤怨恨。她从出生起,便在别人的牵线下生活,予取予求。现在的她一个人了,再没人向她索取什幺,那她又想做些什幺,得到些什幺呢?
过去的十七年中,她唯一学会学精的便是取悦别人,同时也取悦自己。性爱于她而言,是她所能做到的,最有快感的事。
扶烟开始看书,同时也上了些学,培养了一些爱好。她开始画画,跳舞,钓鱼,社交。她认识了一些人,谈了几次恋爱,其中很有几个情至深处,想要禁锢住她的,却都莫名没了后文,也没再见到了。其余的则都称得上好聚好散,仍然能作为朋友偶尔来往。
一年之后,扶烟已经成为了所在城市中,上流社会里最有名的交际花。让她如此知名的除了无人堪比的美貌,还有她颇有些来者不拒的作风。她爱热闹,爱亲密,一根线引向另外一根,不知不觉已织成人际巨网。
她第一次见到令学俊,就是在一次朋友举办的宴会上。衣光鬓影,觥筹交错,数十座华美的水晶吊灯在天顶辉照,人们几近晕眩地在厅中旋转来去,衣饰杯盏流光溢彩,熠熠生辉。而她在人群拥簇中不经意地回眸望去,却一眼就看见了他。
他生得实在很像令洗筠。
在扶烟意识到时,她已经穿过人们,走近了令学俊身前。从他一瞬不瞬望在她身上的姿态来看,他也早已关注到了她。两人各手中端着半杯酒,面对面地站住了,视线胶凝在一起,一时静悄,等时间流过半晌,才都忽然方醒一般,看着对方,一齐清清脆脆笑了起来。
在之后的愉快交谈里,扶烟得知原来令学俊是令洗筠嫡亲的侄子,因为公司有一个重要项目需要洽谈合作,才乘机出国来到这座城市,又顺应合作方的邀请,参加了这场宴会。
那次宴会过后,令学俊立即开始热烈地追求起了扶烟,而扶烟也没什幺犹豫,很快便与他确定了恋人的关系,并邀他住进了公寓同居。
这是扶烟第一次如此投入一段恋情。在她曾有过的关系里,她总是随波逐流的那一方,没太多欲望,也没什幺深情。她要的只是些许陪伴的温度,喧哗的热感,至于是谁陪伴,是谁组织,并没有太大干系。
但令学俊不同。扶烟见不到他时会思念,见到他时会喜悦;见他开心她会开心,见他忧郁她也会沉默。她开始学着照顾他,打理他,化作一捧软水,温柔地抚慰他,热忱地缠绕他。
她觉得自己爱他。这难道不是爱幺?
扶烟和令学俊在一起了四年。
这四年里,令学俊并不一直和扶烟一处,常常是陪伴她三两个月,就要回国去住上半年多。他的父母,令洗筠的哥嫂,待他十分严厉,尤其是他的母亲。令学俊之下还有着两个弟弟,是他的父亲和婚姻外不同的女人所出,与他相差也不过两三岁,底下明争暗斗,腥风血雨,都是老生常谈。
令学俊因彼时出国谈成的项目,在兄弟中算是领先。这四年来,他只敢借视察项目的借口每年来国外待上两三月,除此外再没敢做,敢说的了。
扶烟对此没有十分在乎,她只为两人不能一直在一起而感到眷念。在令学俊不在的日子里,她依然赴宴,玩乐,画画,钓鱼,但没再和别的人发展关系,独自在家,倚窗看灯时,便有些渗透骨髓,难以磨灭的寂寞。
就在这样一个夜晚,扶烟看到了令学俊订婚的新闻。
画面里的令学俊挽着自己的未婚妻子,看起来冷峻又寒俏,十足是个自信强硬的商业精英,若非如此,他也不会比韩绍康更加神似令洗筠。但在这样无懈可击的外壳下,却是怯懦贫匮的软肉。
在例行通话的时间,他的铃声如约而至。这个隔洋的电话里,令学俊先是低声关心了扶烟最近的饮食起居,又询问她开支还够吗?要不要他转些钱到她卡里?被拒绝后,他停了一停,两人之间静悄下来,扶烟蜷着双腿,偏头望向窗外星点明灭的灯火,心中有些许空 -
然后听见令学俊说:“烟烟,你不要离开我。”
扶烟没有说话,于是令学俊只能继续说:“我…我要结婚了。烟烟,我没有法子,是我对不住你,我会补偿你,钱,珠宝,无论什幺,只要你要,只要我有…烟烟,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好不好?”
在与令学俊分手后,二十二岁的扶烟又回复了纸醉金迷,万花丛中的生活。从前的她觉得这样已经很好,已经足够满足,但此时的她无论再热闹,陪伴的人再多,也仍旧感到寂寞。
于是她学会了吸烟。当觉得冷时点上一支,看着橘红色的火星缓慢燃烧,便好像也从指尖汲取了一丝温度,从死中活了过来。
这样的节律持续了一年多。直到一天,她忽然受到一位律师的来访,西装革履,金丝眼镜,不像是玩笑的人,拿出的也不像是玩笑的文件,但他说 -
他说:“令女士在生前立下了遗嘱,将她名下的一部分资产交给扶小姐您继承,其中包括不动产,基金,珠宝……”
他说了很久。扶烟安静地听完他说的话,顺从地签署了所有文件,然后邀请他留下来。
她实在是个很美丽的女孩,即便在这两年里消瘦了许多,但也只使她愈沾染上一种脆弱苍白,薄花碾泥的美感。极少人能够拒绝她;律师也没能。
她仰面躺在床上,乌黑的发藻丝般铺撒在枕间,身上的男人投入地驰骋,而她睁着眼睛呼吸,却像是已经死去了。
男人陷入酣眠后,扶烟赤裸着在床边略坐了坐,然后站起身,踩过冰冷的地面来到了阳台,迎着星点灯火,抱着手肘,慢慢抽完了最后一支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