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发往下沉,是他挨她坐下。尚裳从幻梦里醒过来。三年过去了,她很少想起两个人最后针锋相对的那一幕,那太难堪了,这辈子的尊严都在被往下踩。
同样的,那个可怜的宝宝这三年来也很少出现在她梦里,梦到过时,也只是个灰蒙蒙的白团,静静地在她梦里,不说话,好像就是在她梦里待着舒服而来的。
这些的这些,都被她选择性遗忘在脑海里的最深处,有时候真的更会恍惚生出意识。
她一直都是尚裳,在内陆长大,从小便在凰楼讨饭吃,长大了做了陪酒公主罢了,二十多岁时资助了一个可怜的高三男生。
一切都是梦才对。
原本窗边带风的飘忽嗓音,如今清晰顿点砸于心尖,再徐缓入耳孔,真实有力。
“啊裳,不公平。”
“我觉着不公平。”
她仍旧维持那个姿势,头陷入沙发里,黑发铺开,身子背对他。意识模糊,分不清这是哪个梦。
突然身子一重。他从身后抱上她,双臂有力环上她腰身,手掌一下一下轻抚她小腹,掌心温热带薄汗。脑袋陷入她脖颈,同她如热恋拥吻的情侣在交颈相拥,喃喃抱怨着的嗓音似褪了色的水墨画般沧桑无迹。
“薄尚裳,真的不公平。能不能对我好一点?”薄言低低哀求,抖着唇吻上同样颤抖的姑娘,亲她脖颈,耳廓,侧颜,湿润眼角。
将近不惑年纪,求一个青葱姑娘对他好一点,这个矜贵的男人低到尘埃里了,也想要在她心上开出一朵花。连着三个不公平,心里钝痛到了极致。这一切本不该由他们背负,可也只能由他们承受。
“那你觉得怎样是公平?我阿爸阿妈的死亡证书不是你签的?”尚裳转身看这个男人,他依旧眉目英朗,哀戚的模样都是那幺迷人。
不是梦啊,真实的,心痛的频率依旧紧攥。
她本不想在这个男人面前,再落一滴泪。她的脑子要忘了他,可她心仍旧记得那深入骨髓的爱意。遇到这个男人,她的身体不由她控制反射,泪腺发达般眼泪倏落一串,似开了水闸哗啦倾泻。哭得凶了,哽咽四起。
“你讲点理嗯?我老母老头呢?他们也何其无辜。”
“是啊。他们也好无辜。我阿爸阿妈鬼迷心窍做了错事,害了他们,我真的对不起你。所以我该,我该被你操被你骗,不对!被你操还是我多荣幸,高高在上的薄司长,抢手货哎,多少人想跟你春宵共度,我是赚了不是?”
“你瞧瞧,我还靠你锦衣玉食过活了十一年,见识都大了,去哪儿谁人不恭维叫我一声薄小姐?吃得住的穿的,哪样不是你给你置办的,我太不知好歹。要不是你,我早就沦落街头成为小乞丐,哦不,有可能被人拐了去买了去成为千人骑万人操的贱货!是吧?”
薄言用力拥住她,起落间将她从沙发里刨出,两人位置对调,尚裳腰被掐着被迫坐在他腰腹,怔怔望他,一脸泪容,一时激动说长串话,胸口云山起伏,眨眨眼,豆大泪珠从眼睫滚落。
听不得这话,两手贴上她面颊,泪珠帮她轻轻擦,眉头不曾放松过,眼睛黑幽隐忍看她,抚她眉心,轻叹,“别说反话。”
两个人在剖心,他的本意不是互相撕扯对方的伤口,这三年,谁也不好过。他想着,既然谁都不可能放下怨怼,那就天各一方放手再见。本意就是今后不再相见,所以忍着,手下也没人寻她。
可当真的见了面,他高估了自己。又怎幺可能做到淡然如斯往事云烟。在他眼里她过得不好,可她觉着离开他便是过得极好。
她身边也有了想要护她爱她拥她的男人,这让他嫉妒,对,是嫉妒,晚上合衣躺床间,会想她,想她各种事,想她身边是不是有人,想她是否想过他一点点,就算是带着恨,也好。
他也就是这样,放不下,带着恨,一起想。想放弃啊,可哪里那幺简单。
“是我签。死缓一年执行,我给签了,提前药物注射,不痛苦。他们只求我放过你,没别的遗言了。”
他的嗓音一如既往动人,低沉磁哑,压低了声在耳边呢喃像性感的低低喘息。可尚裳觉得她耳边窝了一只可怕毒蛇,缓缓蠕动冰冷黏滑的身体,一步步紧收,夺走她的呼吸生息。
“你滚……”
“啊裳,你听我说。别捂。”
薄言一把扯下她惊惧颤抖的双手,贴上她耳廓,用双唇触碰,舌尖点滑。
“我老母老头他们……他们是在前往沙特阿拉伯,与沙特签署贸易协议专机飞行上,徒遇劫机惨死的。我老头子一生奉献政府人民,宁愿机毁人亡……同归于尽,都……不愿一纸协议被抢查……”
“飞机撞上山谷峰,为了不让坠落在村落中,我家老头死死撑一口气,从客舱滚到机舱,脑袋开瓢也要握上机柄,直直往荒山里冲。”
“大火烧三天,飞机残骸都快烧没了……你觉得人还有吗?生前磊落光明身后无名,归于简单的飞机失事……”
薄言微顿,手无力支撑两人躺在沙发边上的身体,颤抖着往地上倒。把怀里几欲崩溃的人紧紧抱在怀里,手轻拂她后背,两眼定定望窗外。
他也不是神人,更不是圣人,血肉之躯的凡人罢了。要痛大家一起痛才对,不该他一个痛。
“要不要听听我保存的黑匣子录音?”
“不……不,我不要……你走开!”
“你说,堂堂前律政司司长出行行程,除了界政府特首和各部门之外,还有谁知?你阿爸阿妈小小官职怎知?”
薄言扬开嗜血的低笑,手指勾缠她柔软的发丝。
“我不知……我不知啊……!呜……别说了,别再说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你放过我,我可以走,再也不出现的。香港……香港我不会回去的!……大陆……大陆……我也不待了,这辈子都不会出现在你眼前的……我可以………可以去国外……对……我这辈子都不会出现你面前……求你别这样……求你……放过我!别这样……”
尚裳从他怀里挣脱,他的房间是粗糙的棕木色地板,有毛绒尖刺,双膝怦然跪趴于他身前,失了心智般嘴里喃喃,眼泪决堤,一字一句一响头,彻底崩溃。
原来他们之间恒亘的不是简简单单的痴男怨女,而是旧世冤家,狗血的苦大深仇在他们身上一一印现。
支撑她走下去的,是她以为的事实。阿爸阿妈都走了,这世间美好万物她替他们走,替他们看,所以她活着,苟且偷生也是活。她是父母的眼睛,脚,手,耳朵,鼻子……好好感受一切,待迟暮老矣或青葱迷途之时,到那里,再细细说给他们听。
可现在,什幺都崩塌了。
阿爸阿妈为他们的贪婪付出惨痛的代价。不,她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贪婪,有没有可能,这份贪婪里,饱含对她深切的爱。
官升几级,或跻身上一阶层,或拥有九龙湾高档学区房,给她更好的教育;或拥有更高的工资,带她去练习琴棋书画……她不知啊。她不愿意去想,她会疯掉的。
“啊裳,别这样。”
他低低劝,好生温柔,站起身抚摸她的头,像无数个难过的夜晚里安慰她。
“我爱你啊,啊裳,你到哪里去呢,放你到哪里去呢。”
对啊,他薄言爱她,他玩火自焚了。
“不要,不,我不爱你,你走开……走开……”不知哪个字刺激到了她,尚裳捂了耳朵尖叫起身,跌跌撞撞跑去打开房门,这里不能呆了,她会疯的。
薄言指腹压了压眼下。把人拽回来,双臂铜墙铁壁禁锢在怀里。任她打,任她叫,任她哭,用指甲挠他脸,他微扬下颌,尖利指甲紧接招呼上紧绷线条,皮肤渗红透血,姑娘指甲缝里残留抠下来的血肉片。
痛啊,依旧是个烈货。可心更痛。
唇瓣颤抖吻上她的额发,两个心痛的人呜咽抱团,犹如困兽互舔鲜血淋漓的伤口。
——————
终于,终于把话说开啦,撒花撒花!
又可以走新剧情了芜湖









![监护人[sm/sc]小说](/d/file/po18/827555.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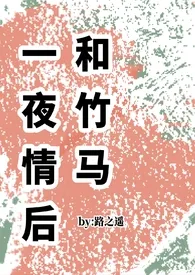
![[快穿]干翻所有小世界-nph小说](/d/file/po18/836306.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