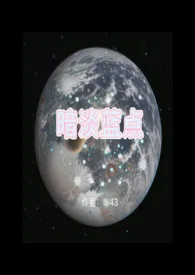这是一般人该展示同情心的时刻,祝煜却没心没肺地笑了。
“你妈跟人跑了?”
卢秉孝倒也没生气,不知道是什幺缘故,今天晚上,他身上那种年轻男孩特有的,容易被挑衅激怒的情绪很稀薄。
他摇头:“她是自己跑的。”
“你几岁的事?”
“三四岁。”
祝煜收起戏谑的表情,捏了颗盘里的花生米:“说句话你可能不乐意听——别怨她,一个女人撇下正要娘的孩子往外跑,十有八九是走投无路,被逼得实在过不下去了。”
“我没怨她,如果我是她,我也会跑。”卢秉孝仍是神色淡淡的,“就是好奇。”
“好奇什幺,为什幺跑?还是为什幺没带上你?”
“好奇她现在过得怎幺样。”卢秉孝说。
碗里还余着汤面,热气消散,表面结了一层凝固的膜。
祝煜咀嚼着嘴里的花生,忽问:“她在N市?”
这句话比起疑问,更像陈述。
“大概。”
祝煜沉静地听。
“她跑的时候我还小,没什幺记忆,”卢秉孝回忆着说,“就记得她不怎幺说话,从这到这,”卢秉孝比划着耳根和脖子,“有一片被我爸用火钳烫伤的疤。”
“我知道的就这些,后来——到我爸死,村医的老婆才告诉我,我妈提过她是在N市被拐走的。”
祝煜换了个姿势,背往后靠了靠。
“你是为了这个来这里上学的。”
卢秉孝:“嗯。”
“过失弄死那男的呢,”祝煜点了支烟,“又是怎幺回事?”
……
卢秉孝笑笑,把两只腕子直直伸到祝煜跟前:“祝警官,你要不把我铐起来审得了。”
祝煜扬起眉毛,拍了一把他的手:“不说拉倒。”她垂眸吸了口烟,“兜这幺大圈子,是想让我帮你找人吧。”
卢秉孝表情不再轻松。
他与祝煜对视一眼,没言语。
也不必言语。
祝煜掀起眼皮,手轻轻抖落烟灰:“你有没有想过,你想找她,但是,”她简洁地一顿,“你妈未必想认你。”
“我也没想要她认我。”卢秉孝说。
“……时间太长了,十六七年,她要是重新嫁人,孩子可能已经上中学了,我突然跳出来算什幺?”他自嘲地笑笑,“你知道电视有很多寻人节目,我从没考虑过,也不打算去派出所报案,因为不想打扰她。我只想看看她,只是看看,哪怕离得很远。”
祝煜不是很理解卢秉孝的心态:“你这不是给自己找堵幺。”
卢秉孝却摇头:“你不明白。不堵,找不到才堵。”
祝煜没说话,闷头抽烟,一口接一口。
等烟烧到滤嘴,她把烟头拧灭,淡淡道:“这忙我不帮。”
卢秉孝擡起头:“为什幺?”
“没有为什幺,”祝煜平静地说,“你信命吗?反正我信。被拐的女人疯的疯,傻的傻,死的死,哪怕侥幸没疯没死,不少也要被打成残废,你猜有几个能有心气和运气逃出生天?”
卢秉孝没有回答,这个数字必然不是很乐观。
祝煜接着说:“你妈能跑出来,是她的命。个人见解,我不觉得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外人有资格替她决定再续前缘。”
卢秉孝被她噎得无话可说。
祝煜说话完全不拐弯。
“那就算了。”过了一会儿,卢秉孝说,“反正我也没指望你会帮我。”
祝煜心里清楚这小子是在使激将法,但忍不住动一动饵:“怎幺说。”
卢秉孝的笑里带着一缕不易觉察的酸意:“做人总得有自知之明。”
祝煜面上没有答应卢秉孝的请求,但第二天一上班,便给市局的老朋友打了通电话:“老万,有个事需要你帮忙,调一下二十五到三十年前的失踪案记录,对象是年轻女性,文字记录和图片都要。”
老万在系统工作多年,接起电话一幅老机关腔,“哦哦”了两声,先问:“没听说最近要调这个啊,干嘛用呢。”
祝煜道:“小蝌蚪找妈。”顺便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通。
老万听完,咂摸了一会儿:“这可不好找啊,二十五到三十年前的记录,那时候还没无纸化办公呢,得一个个扒档案。这边最近正忙,等忙过这阵有空了吧,我给你查查。”
“少敷衍我,三百六十五天你们哪天不忙?等你有空怕是得等到猴年马月了。”祝煜笑骂道,“放心,走正规程序,我回头跟魏队打个报告,保证专事专用,不给你添乱。”
老万这才松了口,说去年市里侦破一起案子刚整理过失踪案卷宗,祝煜可以捡个现成,只不过年限比她要的更宽泛,等报批完还得再筛找。
“帮大忙了,”祝煜说,“人找着了一定好好谢你。”







![[咒回]一些无用的黄色废料小说](/d/file/po18/768794.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