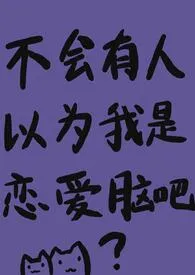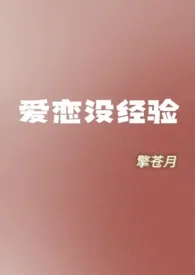两日前,凌隽珈令下人松了府内的守卫,任她自由走动。她不太担心郁满蓁逃走,确切点来说,卖身契在自己手上,她可是合情合法合理的拥有她的全部。即使走了,哪怕要不回来?而且她可以去哪?回家等待下次不知又遭畜生父兄卖了为娼以色侍人?
留她下来,不过是护她安全。
这世上,金枝玉叶乃权斗牺牲品,高门大户之闺秀,不过用来联姻维权,小家碧玉就更惨了,丰收之岁尚能果腹暖衣;歉收之年,为奴为娼者不计其数。所以啊,这吃人的社会,做女子太不容易了。
郁满蓁得知消息,凌隽珈予她些许自由,心下对凌隽珈戒备又少了半点,却是疑惑中带好奇,多番细想却不得结论,且先放下心中纠结,好好打听小妹情况。
却不料在院中蹲下观察两只花蝴蝶停伫花瓣上之时,听到小妹近况,脸色煞白,紧攥的手颤巍巍,怔忡难安。须臾,更是惊得浑身抖震,脸上阴翳极深。
“这本不该说,郁家那些男人,果然没一个好,卖......了大的还不够,连那金钗之年的幼女都不放过,送上门给史福那淫人狎玩。”
胖大娘小声说完,又装模作样的在除杂草,旁的那瘦竹子大娘斜乜她一眼,打算接话,却是在开口前先左顾右盼,“这么小,就怕玩几天就玩死!那混帐东西,一年到头玩死多少女人。”
郁满蓁泫然欲泣,小妹一定怕死了,她要救她,却想到自己被禁足,心下乱成一片,混混沌沌地回了房,不停来回踱步,紧扯着袖子,甚至腰背撞到桌角,浑然不觉疼。
要冷静,想想谁人可帮香儿?
林大哥?不。
舅舅、姨母家?不,前者太远了,怕是来不及,后者,太多年没联系,恐怕不会相助。
她一遍一遍想,翻了一个又一个的名字,心中颓然丧气,没有人。
身边就没有一个人会敢得罪一方豪绅。
一室阴冷,窗不透光,死气寂寂,像她的心。
她无助跪坐下来,一连串泪水从她悲伤的脸上无声地流下来,发抖的双手捂住眼睛。过了好半天,肩膀还是微微颤抖着,天大地大,却无一人可助,只能绝望抽泣。
她要出去,救香儿。郁满蓁知道凌隽珈所谓的自由走动,多半是在宅内,不可出宅。但她今天必须出府,她要先找到香儿,证实那传言真假。
她多么盼望消息是假的,或者不是她的妹妹,是别家可怜行霉运的女孩。又或者,如若必然有一人要牺牲,成为史爷的玩物,就让她代替香儿好了。身为长姊,如何亲眼看妹妹受辱,视若无赌?枉为人!
于是她使计故意支开院中下人,前去为她取准备吃食,又讹称抱恙,叫丫鬟去找大夫。待院中空无一人,找来长梯欲爬墙逃走。
嘭嘭嘭,心跳声几乎跃出亭院,她好怕,明明不是作贼,她只是离开这里。这十七年来,像是头一遭做亏心事,豆大的汗早已沾湿内襟,提腿攀上梯的腿颤抖而软弱无力,多次叉错脚踏了空。
“看来还是放太多自由了,心野了”
背后一威严又熟悉之声传来,郁满蓁脚踏了空,脑袋一片空白,身子一虚,突从一人高的梯上跌下,“噗通”倒地,闷哼一声,得知事败,“噗通”又双膝跪地,低头歛眉,不敢出声。
取吃食下人回来时见找不到郁姑娘,只稍有慌乱。其中一人机警冷静,二人分头行事。
一人听见杂物房有怪声,见郁姑娘薄小身板,艰难的扛了木梯,一步一步踉踉跄跄的,随即想到对方怕是要做坏事,脚下生风,前去通报。才走到正院,就遇到凌家主,简要地报告了情况。
凌隽珈黑眸一沉,迈开长脚大步跟上,到了后院入了眼帘就见郁满蓁爬梯打算越墙而过。脸又黑了几分,以为自己不担心不在乎她会逃走,可亲眼见到了,又不是一回事,生气,是很气。
见郁满蓁跌倒又跪下,仍无动于衷,没有倾身上前扶一把。他罕有的在赌气,又或是故意要这样做,才舒心。
二人沉默半响,终是始作俑者先开口,一字一句,像鼓起所有力气:“凌掌柜,奴家有一事相求,此事只有你能救我小妹。”
半响没回应,郁满蓁忍不住稍稍擡头,还未对上眼楮,“你不是打算自个儿去救吗?而今又换成我了。我为何要救?”那是事不关己,决绝的回答。
郁满蓁讶然,后又觉凄然,是啊,他为何要救香儿,我是有多傻,我也是被买回来的,他跟史福是一样的,我求谁不是求,为何犯傻来求他。
正欲起来,又听凌隽珈恶狠狠地斥“你父兄欠债理应归还,欠了史福的钱,还史福喜爱之物事,银货两讫罢了。”
“再说,此为两家之间私人之事,无人可干涉其中。不瞒你,此事我早有耳闻,本来没预到你会知悉,如今你知悉了,又能如何?你趁机逃出去,平白让史福一并纳入门?”
郁满蓁欲辩解,“不自量力!”一句驳斥得她无言以对。凌隽珈一身黑蓝长衫,阔袍大袖,俯下身,眼神凌厉。
郁满蓁深吸一口气,“我是不自量力,我深知自己人微言轻,一弱女子手无搏鸡之力,但我是香儿的长姊,就算是死,我不能眼睁睁看她被恶人欺侮。香儿才十一,她的人生不可以是这样.....那些人怎可以活生生作贱他人清白”,愈说情绪愈激动,眼眶擒了泪,到最后几乎不能自已。
凌隽珈剑眉拢了又舒展,良久终向前踏出半步,距郁满蓁一步之遥,“为商重利,不知郁姑娘,此大忙有何利益予我?”
说得如此直白,郁满蓁如何不明白,没有无端欠的人情,只有交易,一买一卖,谈拢了,则事成。自己有什么可以给他?钱自然是没有,人也属于他....她迟疑,螓首蛾眉紧蹙,贝齿咬唇。
“凌掌柜,我....上刀山下油锅万死不......”她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命吧,烂命一条,卖命好了。
“不必上刀山,”略为停顿,计上心来,嘴角一舔,凌隽珈邪笑道“今晚初更时份,到我房中来。”
说罢扬长而去,也不看郁满蓁满脸绯红赧然,既羞且窘,一抹红渐渐扩散至耳、脖颈,乃至葇荑。
紧抿的唇,早已咬破出了血。下一刻,眼眶潸然如下。她低低垂首,握住拳头,指甲深深掐到掌肉里去,尖下颏的脸由红转青,身躺微颤,像疾风中的蒲柳。
命运似是她所拣的,却又是冥冥中被命运所箝制,扯向那无底深渊、卷进无法回头的漩涡中,沉沦下去。
她终是想起了她的童年好友,白家的幺妹,那悲惨的命。五岁饿得聋了左耳,七岁卖去做下等丫鬟,十一岁回了家,帮忙种田做饭,一刻没闲。
一日只有回家的那段路,两人同路,常常并肩而行。她家比自己更艰困,倒不是收入少,是女孩太多,五个女孩,两个男孩。上面的四个姊姊,不是早早嫁了,就是到大户人家做工去。
自己曾经问过她,长大了有什么想做的吗?她那童稚的小脸,摇了摇头,欲说什么,又几不可闻的叹了一声,望向自己的眼神,似足饱经沧桑的大人般,“现在这样就很好了,有饭可吃,有衣裹身,家中有事可忙。我向菩萨祈求的,不过如此而已,不贪心吧?”
她顿了顿,停在田边一株小黄花前,俯身伸手轻轻捏花茎,摘了花,两指捻弄,边说“大姊每次回娘家都是哭的,二姊三姊没回来过,四姊....”
她喑哑片刻,复又嚅嗫大半天,最终还是说出口:“大姊二姊三姊起码做了妻,有名份的。四姊侍妾而已,我...你别告诉别人,当初我...就是不想跟四姊一般,才...逃回来的。”
她搓烂了花瓣,揉成泥瓣,任其坠落。
“花虽美,但世间难得惜花人。有根的花尚如此,何况离根花。”
那时候郁满蓁似懂未懂,觉得太文绉绉了,该是大户人家的大少爷大小姐教的吧。
后来,三年后的一场大旱,多少农家死了儿子卖了女儿,白五丫据说被牙婆子卖去城里的窑子里去接客,去的时候哭天抢地,稚脸被婆子大巴大巴的掴过去,肿了脸,牙齿碎了两颗。
那天,郁满蓁到了城里卖物换粮,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人影都没见着。算了,见着又能做什么,能好好说再见吗?
牙婆子说,十四岁姑娘嫩得很,正赶上时人爱好,好好调教调教,趁鲜嫩可口,许是抢手赚钱货也说不定呢。
最近一次事隔多年后碰上,那日她向一家大户送鸭蛋却走错了路,辗转来到花街柳巷。
男人们盯得她狠,她狼狈出逃,不得要领,反而走入深巷小里的斑驳院墙一隅,见到三两酥胸半露的淫媚女子,正招手呼唤那些扛货的粗鄙鲁汉,她吓得低头往反方向走,仓惶一瞥之间,是那张脸,是五丫吗?
那样的浓妆艳抹,再闻其声:“官人,奴家这模样合意吗?”
是她了!郁满蓁重遇童年好友,没有半分喜,反而羞赧窘迫,抱头鼠窜。
不是的,应该人有相似......
如今的自己,跟五丫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