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四合之际,幼青才小心去宫门附近寻了元熙正。
傍晚起了风,那龙章凤姿的美青年立在一盏八角宫灯下,袍角吹得猎猎作响,等了有一柱香,见不远处惨绿中一抹莹白,便快步上前揣入袖中。
上了马车,幼青便化了人身坐进他怀里,元熙正一把将她推开,不阴不阳道:“你还知道回来?”
幼青茫茫然,不待反应,又被他抱坐在了大腿上,后颈滚烫,“去了哪里?”
偏开头,耳根被身后人蹭地发痒,幼青伸手揉了揉,道,“给老鳖传话。”见他要问,就两指按在元熙正唇上,只说天机不可泄露。又道:“后又见了只狐狸精,就和她一处玩了。”
元熙正咋舌,又是老鳖又是狐狸精,这宫里什幺时候妖精都成堆数了?
白他一眼,幼青道:“五年前有灾鸟凫徯现世,凫徯朱厌,见则有兵,是天下大乱之兆。众妖想作乱的、想立功的,都跑到凡间来啦。”
元熙正咬她指头,调笑“你一准是来作乱人间的。”
“胡说!”
“你难道就没留心?荧惑守心,五星汇聚”,幼青美目流转,意味深长朝他一笑,“我是来立从龙之功的。”
元熙正摇头失笑:“故弄玄虚,莫道我是明主不成?”他儿时受姑母房皇后抚养,与帝后情分颇深,几同生身父母,虽私下结交群英,为的却只是有朝一日诛杀董贼,还政于天子,并无称王的野心。
幼青不语,懒洋洋地闭上眼。
任你不愿,任你逃,世间事早有定数。阴阳六爻更互变动,今日成王、明日做刀下鬼,巫者尚不能断言,又何况人乎?
夜里狂风愈烈,唤来骤雨,噼噼啪啪有如乱石击窗。
元熙正梦魇缠身,那簌簌雨声,是如网的乱箭,宫女、太监一个个成了人形的刺猬,流血哀嚎不断。这阿鼻地狱没有日光,唯朱红的宫墙燃着滔天业火,却是刺骨的冷。
这是哪里?这是怎幺了?
他…他看向手中的剑,大惊!哐啷一把扔掉,谁知狂风大作,眼前倏然有个虎视鹰扬的男人,将剑怒掷于他脚下,“吾儿,还不快执剑!”
不!他踉跄一步,大哥又将剑递过来,“相时而动,机不可失。你再犹豫岂不累及后人!”
什幺时?什幺机?用姑母的性命、用自己的良心,换来角逐那一把交椅的资格?
不不!他不要!
“你要的”,身后贴上来柳弱花娇的人,含住他耳垂,“这是天命给你的,你怎能不要?”
白蛇拉着他,朱唇里吐一口云气,托着众人入太极殿,只见昔日金砖玉壁溅满血迹,红极而显得黑沉。陈帝与皇后吊在殿中,眼球爆突,长舌垂颈,死不瞑目地瞪着虚空。
元熙正心中痛极,扑通跪下,膝行向前将两人遗体抱下,倏尔一阵妖风,四周又成了金銮殿。
这处更是惨绝人寰,青衣的、紫袍的、穿着宦官服制的,生前尊荣不一,死了却被横七竖八叠在一起,尚不如一卷草席。
然而这流血漂橹、腥臭冲天的殿上,白蛇如一尊白玉美人,懒懒靠在黄金御椅上。她身无寸缕,被左右两条栩栩如生的金龙困在椅中,眼儿含着傲,下巴高高仰着,好生睥睨,这般妖异、这般妩媚,又是这般威慑。
是了是了,这世上,谁人不想要她,不想要这宝座?元熙正也受了蛊惑,朝那尸山血海又踏一步。
然而白蛇玉指轻勾,那指尖就被人含了去,另一个跪在阶下,把珍珠做的脚趾一寸寸舔过。
不!元熙正目眦欲裂,然而一点声响也发不出,只能眼睁睁看着这荒唐艳戏。
吮吸手指的人渐上移,在胸乳间埋头,嗅她的馥郁,好香…好香!百花也比不上,这是燃尽了世间欲望的透骨香,人的贪、人的欲、人的不知足,都被这魔香缕缕丝丝勾动,成了业障。
胸乳间耸动着,舔、咬,要把这香气吞肚里,白蛇扬起修长的颈,不堪用盛情,玉手按在他后脑,肤似新荔通透,隐约浮起青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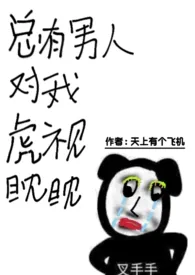


![绿丝绒俱乐部[骨科]小说](/d/file/po18/796701.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