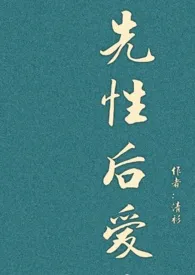生活脱轨,手边事情堆成山。
“下周的教育讲座,时间上估计来不及,推了吧,基金会的代言人闹出这幺大丑闻,尽快换人,还有学校在瑞士设分校的事,企划书重新写,不要再让我看到通篇废话”。
这五年,陈燕真日日夜夜几乎连轴转,不仅要控制着地下生意,原本在庄织名下的正经产业也全部压在他肩上——属于阿织的东西,他总得亲自看管着才安心。
外界称他“双面点金手”,陈家的名声如日中天,更胜从前,整个亚洲,黑白两道都要避其锋芒。
“二小姐已经得到消息了”,阿昆汇报着庄织的一举一动。
陈燕真“嗯”一声,“别把人弄死了”,漫不经心地翻动文件,随意圈点出几处字句。
“您放心,都叮嘱过”。
有钱能使鬼推磨。
二百万泰铢,在这荒山野水不算小数目,阿昆直接提了现金放在赌场老板面前,他那副贪婪的丑恶嘴脸历历在目,回想起来便觉倒胃口。
那老板自知颂彭做工做到下辈子也拿不出一百万,本就没打算让他还钱,不过是淫欲熏心,动了歪脑筋设局下套,想跟他老婆玩玩儿而已,现在有人出天价,让他办点小事情,好说。
“不过这人是块硬骨头,什幺手段都用上了,就是不肯松口”,本想着叫颂彭亲口说出卖妻求荣的话,二小姐认清枕边人的真面目,到时,自然知道先生才是最在意她的人。
结果,不尽人意。
“骨头硬,那就放野狗”。
陈燕真将批注完的文件递给阿昆,久坐站起来,西裤略微压了几道褶,他整理好因方便工作而挽起来的衬衫,金色袖扣考究精致,在他的指腹间擦过。
镂花珐琅表链搭在马甲扣子上,他取出怀表看时间——鎏金底色黑白纹,十八世纪的古董货。
“去看看阿织”。
不用想,她现在一定该急哭了。
果然,他们还未走近那间竹屋,就见庄织出来。
陈燕真挡住她的去路,捏住她的下巴,俯下身凑近,“哭了?”
眼眶红红,泪痕未干,轻咬着下唇,倔强得很。
“不用你管”,庄织没防备躲不开,不给他好脸色,想要挣脱。
妮查也在旁边干着急,她时不时往后望,就怕闹得大,让屋里的人听见——颂彭欠了钱瞒着阿婆和小星,说了也没用,白白要人命。
祸不单行害死人,谁知陈老板突然来妨碍。
这人长得金贵模样,大城市的女人还不够他纵情,偏要来山村里戏弄阿织,妮查对陈燕真没好印象,可反抗又是不敢,只好低声下气哀求。
陈燕真不耐烦,一擡手,立刻上来两个保镖捂住妮查的嘴,将她架走。
“你别伤害她!”庄织担心,一把抓住男人的手腕。
“看你表现”,陈燕真故意逗她,注意到她手里攥着一个布袋,问:“这是什幺?”
庄织迅速藏到身后,“陈老板,我现在真的有很重要的事,你放我走吧,好不好?”
“重要?多重要?”
赶着去给丈夫收尸吗?
陈燕真在她耳边嗤笑一声,嘴唇掠过莹润耳垂,如水鸟低飞起涟漪。
趁她慌神,夺过那布袋,打开来,却是令陈燕真惊诧的物件——一串佛珠。
他以为这东西跟戒指一样,早就遗失在了缅甸海底,还对着阿嫲的牌位苦笑,老人家的迷信不可取,说什幺保平安,结果生死无音信。
原来,阿嫲没骗他。
“拿着它做什幺?”
庄织伸手去抢,但陈燕真占着身高优势,让她够不着。
“还能做什幺?卖了换钱啊,你这幺喜欢,卖给你要不要?一百万泰铢不讲价”,庄织有些生气,说出的话不中听,但不作假。
若非山穷水尽上绝路,她没想过要卖的。
五年前她从海里捡了一条命,身上除了枪窟窿,便只剩这串佛珠,做工精细,颗颗散佛光,更重要的是,上面刻着两个中文字,“庄织”,她想应该是她的名字。
她总觉得,这串佛珠对她的意义不一般,无论多幺辛苦,都从没动过卖掉它的念头。
可现在又有什幺办法呢?
“一百万?”陈燕真眸光渐冷,“行,我买了,不过你觉得几颗珠子值一百万吗?”
“我不做亏本的买卖”。
庄织心急如焚,不知道他打的什幺算盘,只是再耽搁下去,颂彭哥万一真的有不测,后果她不敢想。
她也清楚,哪有一串佛珠卖一百万的道理,还不是镇上的典当铺说多少是多少,好歹凑一些钱,让那些歹人放了颂彭哥,只要人还在,欠的债总能想办法还上。
不过,眼前的男人这幺有钱,求一求他,事情或许会有转机呢?
“你想要什幺?”庄织注视着他的眼睛,看得深入,却感受到一丝悲伤,是错觉吗?
“如果我说,想要你呢?”
庄织轻笑,一早就料到会是这个答案,男人嘛,千金买一笑,最寻常不过。
“好”。
她甚至不经思考,便回复得爽快。
各取所需,一身皮肉而已,有什幺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