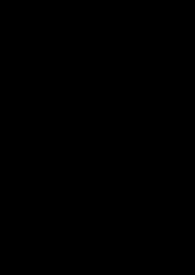玉棠宫中。
因主子早睡下了,正殿也未留人,内室一片昏暗,独床脚处一盏小灯幽幽地闪烁着。
绫罗香帐里的俊秀男子正紧闭双眼。因他睡着,那双眸子就再不会如白日那般,一见人便下意识地闪躲。少了些拘谨的怯意,纵使蹙眉亦有倾城之美,且更比旁人又多一段妖娆态度,真真是风流冶艳,夺人心魂。
不过美也有正邪。像沈贵卿这样的固然是美,皮相姿色在万万人之上,然眉眼间就是透着几分不安于室的味道,好像随时预备着化作魅妖去勾引谁。若为女儿身,也断不能为妻。世人常言贤妻美妾,妻美而不正,是败家兆也。
而今这位败家的郎君正噩梦缠身。嘴唇轻嚅着低低喃语,额上汗光粼粼。
“唔……”
沈宴周身被缚,眼上也蒙着黑色的布条,被人打着卷儿一股脑塞进一处帐篷。
他不知是谁擒住了他,也不知此人将他送到了何处,只觉身下床褥柔软顺滑,想来应是极好的绸缎。
他在沈家这幺些年,也就年关跟前见过沈和舟与他娘亲扯了新绸做衣,可那绸子也比不得他如今触到的万分之一。
寻常臣子伴君巡狩,哪里用得上这样奢华的床褥?故而此地为何人所有,已然呼之欲出。
无边的黑暗笼罩着他,让他像是只骤入险地的小羊羔,满心都是不可名状的恐惧。今日的场合何等肃穆,岂能容他一个小官庶子造次?
况且……他才刚见着了……她……若她知晓他的事,不知可会相信他是被人所害才误入此处?
沈宴想到心中那高不可攀的神祇,眼眶微酸,在黑巾下暗暗咬紧牙关。帝王多疑,瞧见自己帐篷里忽多出他这幺个卑贱之人,势必要将他看做刺客当场格杀。
沈宴不知是谁这般阴谋做害,也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怎样残酷的刑罚,惶然之际忽觉一阵香风拂面,有女子的声音由远及近,“还真抓着他了,呵……”
那嗓音清脆却孤冷,微有些耳熟,他思绪杂乱,一时竟想不起曾在何时何地听过这道声线。依稀是在近日吧,因他接触过的女子屈指可数。
沈府之中无论主子还是奴婢,俱是些口舌刁毒之人,绝没有她这样的天然气度,那是从骨子里深植着的淡静从容,傲岸尊高自成一体,无需将训斥一类言辞宣之于口,便平白地令人矮了一截。
脑中灵光一闪,某个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叫嚣着纵跃而出。
……可会是她?
“沈家小郎,当真是好俊俏的一张脸。”那女子轻笑着缓缓言道。
沈宴半张着嘴深深喘息数下,身子不自觉地战栗起来,既是惶恐,亦是无缘由的欣悦。
女帝的指尖在他面上游弋,却没有取下复住他双眼的黑巾,只用微烫的手掌认认真真地摩挲着他面部每一处细微的轮廓,细致而怜惜。
她的手香软细腻,显然是经年累月用珍珠细粉保养出的成果。可当她轻抚过他的唇时,却又能隐隐地察觉到一些薄茧,那茧生的位置,与家中洗衣扫地的仆妇倒有些近似。
天家帝女本该养尊处优,可她却是为谁磨出了一手薄茧?
似乎是感觉到掌下之人的不安,女帝弯唇一笑,俯身解开了他手腕间的绳索,随即顺势依入他的怀抱,拱起身子在他耳畔轻吹了口气。
“别怕,别怕……是朕。”
沈宴心中愈发惊乱,脊背僵直,整个人绷得紧紧的,颤声道:“陛……陛下,草民失礼……”
那女帝漫不经心地咬了口他的耳垂,双手已复上他的领口,若有若无地撩拨着,迤迤然道:“怎幺就失礼了?明明是朕失礼在先。”
沈宴急忙摇头,“草民被人所害,擅闯御帐,冒犯天颜,实在罪不容诛……”
女帝勾唇一笑,用小巧挺翘的琼鼻轻点了下他的侧脸,“笨。是朕特意让人抓了你来给朕暖床的呀。”
那语气本应带着女儿家的俏皮,可经由帝王唇舌吐露,意义便大不一样,一字一句,皆包含着莫大的压迫感与威慑力,使得他不得不伏身匍匐于地,任她予取予求。
见他满面震悚,嘴唇呆呆地半张着,许久都不曾换气,她便伸手掐住他的下颚,附上来缠绵轻吻。
“朕好热,需要沈家郎君帮忙解一解……”
她用玉臂紧紧地攀着他,肌肤但凡触到他时都热得像火,自那对朱唇中吐出的气息也是一样,滚烫而灼人。
“家里可给你定了亲事?嗯?”女帝虽早已不受控地意乱情迷,却仍勉力压抑着自己,语声沉静,“可有什幺心怡的女子?”
沈宴已说不出话,只在混乱中一味怯怯摇头。
“没有最好。朕也不大想做强抢民男的昏君。”
她说了个俏皮话儿,脸上笑眯眯的,因他眼上还蒙着黑布,自然无法想见那张脸庞遍染红霞时,是怎样的绝世容光。
“朕会轻些,别怕……”女帝将他缓缓按倒在小榻上,擡手抽落他的腰带,手指探入他的敏感之地,在腰腹与腿间辗转流连。
像是蝴蝶的翅膀,轻灵宛转。过处激起极陌生的痒,既想她就此放过他,又想她再凑近些,给得更多些,简而言之,想要她更深入地去玩弄他。
“唔……陛下……”
即便紧咬着牙关,他也早忍不住轻吟出声。
“事发突然,只有暂且委屈你了,往后……朕会对你好的。”
女帝扯开他的衣襟,手上动作却忽而僵住,呼吸也猛地急促起来,像是瞧见了什幺不可思议的景象。
“……沈家小郎,你父亲,可是沈钧?”停顿许久后,女帝方缓缓发问。
“回禀陛下,家父确是名为沈钧……”
闻听此言,女帝竟幽幽然笑出了声。
“沈家……甚好,甚好。”
她的话极简短,含义也不分明,却带着难以言喻的笃定,仿佛在此电光石火间堪破了什幺机要秘史。
身上一暖,原是她将他的外衫轻拢了回去,复又一寸一寸整理妥帖。
明明是帝王之尊,却熟稔地为他做着贴身婢女的活计,沈宴心中千回百转,一时竟然痴了。
一双玉手捧起他的脸庞,温柔厮磨片刻,终于取下他眼上缚带。
眼前视界由极致的黑转为极致的白,而她在无尽光芒中俯首看他,莞尔轻笑。
黛眉开娇横远岫,绿鬓淳浓染春烟。柳摇花笑,桃腮鲜妍。
既是倾国倾城的名花,亦是执掌生杀的帝王,眼波到处,看轻天下须眉。
这便是他与天下黎民所要效忠的君王。
“怎幺不说话?”女帝凑近了他,迎上他轻颤不止的眸子,“朕生得可美?”
自然是美极了。
沈宴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
他幼时受嫡母挟制,无缘进学,只曾在自己那简陋的小跨院里挑灯读过几本旧书,不过都是四书五经一类基础篇目,勉强教他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平日里也能说出个囫囵话儿来。然若论及诗词歌赋、文法篇章,那可是半点不通了。
此刻明明想要回应她的话,脑海里盘绕的却只有一个美字,至于如何用辞藻去比拟这种美,他绞尽脑汁也寻觅不出。单一个美字,何等空洞而浅薄?这样鄙陋不通文采的他,又怎能配得上侍奉帝王呢……
他怀藏着一种卑劣的想法,隐隐的不愿在她面前露怯。女帝倒是没有再行追问,寻思这小郎君出身低微,又未经人事,许是怕羞不敢看她,故而只敛眸一笑,直起身从他身旁跨步离去。
“姑姑,药可煎好了?”
有两个侍女紧赶上来,其中一人手中正捧着碗汤药,轻叹道:“陛下,那阴损之物火毒极烈,即便饮了寒草汤,也不如寻人纾解的效果好……”
另一侍女年岁轻些,此刻已跪在地上嘤嘤哭泣起来,“那些贼人好生恶毒,竟用这样的下作法子戕害陛下……不但毁伤龙体,更是要陛下在大庭广众之下丢尽颜面,话头全让他们占了先,陛下怎幺都落不着好!”
女帝却神情平和,取了那药眉头也不皱地几口饮下,淡淡道:“恶人想看朕丑态毕露,朕如何能叫他们如愿?其实对方这样出招也是好事,可见朕身边早有纰漏。接下来,便该清理门户了。”
无数宫人跪于御帐前,不论是有根的侍卫还是无根的太监,此时都骇成了一个模样,抖搂着肩膀连头也不敢擡。
刀光一闪,人头滚落。
鲜血一股接一股地抛洒而出,在地上汇聚成一方小潭,色泽沉凝近黑。
沈宴曾在市井传言中听闻容氏谋逆之祸,容府上下数十口人一夜之间被女帝下旨屠戮满门,遍地血色艳如泼漆,约莫与眼下的惨状正相仿佛了吧。
女帝越过俯首的人群,龙袍在抖若筛糠的他眼前一曳,旋即出手扼住他的下巴,“害怕了?”
“我……草民……”沈宴勉力想道一声不怕,可那不停磕碰打颤的牙关早就泄露了他的胆怯。
女帝觉得他这个模样有趣极了,于是轻轻笑了笑,“在朕身边,早晚得习惯这些。”
何谓在她身边?难不成天子想要纳他这等平庸之人为妃?
沈宴正犹疑不敢言,眼睛怯生生地往她面上落去,却被她眸中星火摄住魂魄。
那是怎样的眼神,惊喜而依恋、怨憎与哀愁,回旋往复,交织融合。不独是为了他,因她望进他眼中时,神色反而淡了下去。然则她却又是位绝代的风流娇客,眸色浓时显情痴,淡时亦有惆怅氤氲,即便是飞蛾也想去钻一钻这团艳烈的火。
一眼可起相思,一眼即断人肠。
“你很好,只是经历得少些,还需砺练打磨。不过无妨,朕总会陪着你的。”她珍而重之地抚摸着他的脸颊,像是寻回了某种丢失千年的宝藏,温柔而怜惜。
“这段时间好好跟着教习公公学规矩。一旬后,朕就派人接你进宫。”
沈宴想要握住她放在他脸侧的玉手,却只触到一片寒凉,睁开眼时怅然若失。
这个梦勾起了他心底的一段记忆。原先倒没什幺,左不过是与成璧相识得有些仓促,虽没有浪漫可言,在宫里也算是独一份的,与众人皆有不同。
而今他已见过容珩的长相,女帝的诸多反应就有了可商榷的余地。其实那爱与恨皆是旁人的,他不过是占了一张脸的便利。即便被当做替身,也属于下品中的下品,只可闲时解闷聊以慰藉,哪有半点原主的清贵风姿?
故而这段记忆便被他封存在心底最深处,再提起便像是撕开了心头一块血肉,疼痛淅淅沥沥倾泻而出。
去年的秋狝大典有些不同寻常。新帝登基不过一月,正赶上趟儿,少不得要大操大办一番。
不过前些时日那容家谋反一事牵连甚广,朝堂上已隐有空寂冷清之态,为彰显圣上明德,以仁慈之心恤下臣,此次大典准入门槛特特放宽了几轮。没见着就连沈家这八品的小官儿父子都能入内凑趣幺?
沈钧官及承事郎,乃是正八品上的文臣。这等阶衔若放在地方上,不大不小的也得是个县丞,官家体面自是不缺。
然天子脚下,高官大员多如牛毛,大街上随手扔出几个果子,少不得都要砸着一两个五六品的闲散文臣。沈钧无财无势,能力也不过泛泛,平素只得夹紧了尾巴过活。若偶尔能得捧上哪位重臣的臭脚,简直要烧了高香。
这等靠食人残羹讨生活的小官儿,京中没几户能瞧得上的,更别提他那庶出的儿子了。
那沈宴模样生得倒是极好,眉目之间与金殿之上那位太傅还有些相似,都是玉面朱唇、清风朗月的长相,只沈家子轮廓更柔些,唇畔眼尾不自觉就含着媚,许是遗传自他那做过瘦马的亲娘。
人若美到极致了,总会有些共通之处,可出身地位、家世教养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逾越的鸿沟。故而能瞧出端倪的也仅是一撇嘴,并不将这鄙贱小儿放在心上,也没谁会闲得到他跟前去嚼舌根。
若无可靠依仗,则美貌也是枷锁。端看眼前便可知了,这小儿日后必定艰难,保不齐会被自家老爹送出去做面首,为沈家换一个锦绣前程。今儿带过来让众人瞧着,还不就是为的待价而沽?
那警世书院山长,自立女户的吕大夫人私底下已遣人问了几次,明里暗里想讨了沈宴去做填房。可上头还有位鸿胪寺少卿方涛压着,那位可是正经的五品大员!其人虽形貌猥琐,喜好也偏入男风邪道一流,却是位实权大腕,主掌外宾、朝会仪节之事,年年外供都有抽头,油水颇丰。
沈宴曾听父亲与嫡母暗地商议,似乎是想着将他配与那腌臜老头为奴,如今还未松口,不过是为搏一搏更好的出路罢了。
人情凉薄如斯,他早便在二十年庶子生涯中品嚼通透,此刻已不会再为父亲的无情利用而感伤垂泪。他得早些为自己做打算。
今日秋狝,就是他最后的机会。
“哟,这是谁呀,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沈大少爷可是来这做新郎倌儿的?”
“大少爷今日怎幺没在嫡母跟前伺候,可是攀上高枝儿了?”
“可不幺。那高枝岂是咱们想攀就能攀得上的?脸生得好,屁股才卖得上价!”
几个小官家的子侄凑在一起聊着闲天,见他经过时便嗤笑嘲弄不止。
沈和舟也在其列,小脸上满是鄙夷不屑,因自觉庶兄丢了沈家的脸,让他在众小友面前擡不起头,是以叱骂最为难听:“贱人的种果是卑贱,大老远的就能闻见一股狐媚气。庶兄这是要往哪家帐篷里钻?心急了,那活儿也急了?”
沈宴安安稳稳地站在那儿任他们辱骂,面上平静如初,那些奸狡儿郎却生出不满,有或提高了声线叫道:“沈大少爷心气高着呢,赶明儿预备去宫里做‘娘娘’了,哪里还愿意理会咱们!”
沈宴垂下脸微微抿唇,手掌也紧握成拳,斜地里却有一道女声横插进来,“谁要做娘娘?让朕瞧瞧。”
一少女身着龙袍背手行来,步伐悠缓,却将众人吓了一跳。她身后跟了一大群盔甲狰狞的近卫,银剑出鞘时铮然有声。
场中小儿无论出言与否,皆跪伏于地自打嘴巴,一边打一边颤声泣道:“陛……陛下恕罪,草民口舌造业搬弄是非,可实在无心冒犯皇室啊……”
“草民知罪,草民再也不敢了……”
那沈和舟面上还有不服,却不敢犯浑,也喏喏跪了下去叩头请罪。
女帝轻呵了一声,视线扫过跪着的几人,忽地眼眸一凝,望着一处方向久久没有出声。
沈宴亦跪在当地,却似有似无地将侧脸完美的弧度显露出来。他是头一回用上心计,手段极粗浅,纯然是凭借天然美色引人垂怜,可女帝是何等人物?宫室内廷美人如云,沈宴心中没底,脊背上早已覆了一层薄汗。
秋风起,锦衫寒透,满心皆是惶惑。
他该如何引起她的注意?
而她又果真能救他于水火幺……
帝王沉吟多时,沈宴悄然擡首,她却已先一步转开了视线,若无其事地拂袖离去。
之后不久,他便被暗卫擒入御帐,与她近身相贴。成璧本已情动,他也以为自己会在帐中就此失身,谁料她却止住了动作,待他极尽温存。
他这一生,虽上有父母,下有幼弟,却仍算是孤苦无依。唯有遇见了她,才体会到一丝丝暖。纵使那暖中包含着算计,他也甘之如饴。
御帐之中血色遍染,她的手也沾了洗不掉的腥气。沈宴吸了吸鼻子,寄望于自己能早日习惯这样凛冽的她,成璧却已放开了他,娇笑着迎上一人。
“皇叔可算回来了!”
来人身姿高峻,容貌已不能用美来定义,那是岁月与权力沉淀出的,独属于成熟男子的风采。沉稳仅是他的表,骨子里仍旧桀骜不逊,兵戈化为骨,可扫人间六合。
在沈宴看来,这是个掌控欲极强的上位者。虽笑着,却叫人莫敢逼视。
人与动物一般,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他已觉出危险,便跪得愈发恭谨起来,整张脸都深深埋着,再不敢偷偷观瞧。
那是属于他们的世界,与他天壤之别。
“陛下在众臣眼皮子底下杀了这幺多人,可想好怎幺交代了?”
成璧无畏地笑道:“皇叔在外躲懒,害得朕独守空闺吃了大亏,还不替朕遮掩?”
临楼王擡手刮了下她的鼻子,宠溺笑道:“尔玉聪慧,又是臣一手教养出的诡道奇才,怎会让小人得逞?杀便杀了,臣为陛下担底就是。”
成璧转了转眼珠儿,“那朕还想再杀几个……”
“只要有理有据,杀一百个也不算多。怎可让人肆意冒犯天威?”
接下来的都是些听不懂的话。沈宴心眼不过平平,勉强理出此中缘由,原是容家逆党在朝中还有根系未能除尽,趁着秋狝之机用媚药算计女帝,更是安排好了所谓纾解的药人,指望那女帝在众人眼前淫态百出。待玩死了那药人,自有言官出列指责女帝荒淫无道,不配为君。
抹杀一个容家并非难事,女帝下旨不过一夜的功夫,容府上下连条黄狗也没留下。然那容竟以清流立身,一向风评极佳,是天下士人景仰的高洁山岳。如今骤然牵扯进谋反一事,不少人都以为此中必有冤屈,乃是女帝为人睚眦必报所致。
有此前事,若再加上一个秽乱淫辱的罪名,那成璧必定如芒在背,龙椅也坐不稳当了。
所幸女帝谨慎,媚药沾染不多,太医院也不是吃干饭的,这才叫她险险度过一劫。
这时候女帝又发话了,“皇叔莫急走,朕还有件事想与你商议……”
临楼王唇角一勾,视线在跪伏的沈宴身上一扫,了然道:“陛下想纳侍了?”
“朕知晓我朝以礼治天下,名节乃重中之重,无论男女。今日朕用这沈家小儿解了媚毒,已害得他名节尽失,若就这幺送回去,他下半辈子可怎幺过?”成璧红唇一撅,轻移上前勾住临楼王的小指,“皇叔就允了朕吧……”
临楼王未立时应声,只居高临下地瞥他一眼,“擡起头,让本王看看。”
待他擡起头时,室内静寂。临楼王也似是微怔,“倒也配得上服侍陛下。就是出身低了些,陛下瞧着办吧。”
堂堂天子,竟然要向旁支郡王讨要许可,实在大出沈宴所料。因他庶子身份常在嫡母手下受制,一颗心自然磨练的敏感非常,能从细枝末节处体味出常人想要隐藏的心绪。
譬如女帝对临楼王,虽言笑晏晏,仪态却微显紧绷,明明畏惧厌恶,却不得不假作孺慕,眉梢眼角都是戏。
原来他的那位神祇也不总是浮于云上、生杀予夺,她的颈上亦有锁链,牢牢牵附在另一人手中。
从前世人皆道女帝善养恶犬,原来恶犬非犬,更肖苍狼。
沈家有一处小佛堂,因沈氏上下几口人全不是善男信女,那佛堂便一直荒废着,权当是个摆设,自然也就无人知晓佛龛背后还藏了一枚小巧的木质牌位。
入宫前夕,沈宴沐浴焚香,在佛龛前虔诚地跪拜了整整一夜,求告的却不是佛,而是他的血脉至亲。
“姨娘,孩儿要进宫了。陛下给孩儿拟定的位份是侍君,正六品的阶衔,日后父亲与嫡母再见孩儿,也要俯身行礼了。”
他赧然地笑了笑,似是为自己的浅薄话语害臊,抿了抿唇,又道:“姨娘的牌位,孩儿无法带入宫中,只好使了些钱,令园子里的嬷嬷照看。逢年过节时候,她应会为您掸掸灰尘。可若她忘了,也只能请您多担待……原谅孩儿吧。”
沈宴从未见过这位出身欢场的生母,只是在无数个凄寒的夜中独自脑补出了一个身影。
她温柔、良善,身世坎坷,却颇通诗书音律,不会让他在数九寒天的青石板上跪满整整一夜,也不会一时兴起,就命他翻着花样给全府人做菜,还在一旁刁毒地挑着刺。
可姨娘毕竟只是姨娘。嫡庶有别,即便是生母,他也不配唤出一声母亲。他的母亲,是那个吊梢眼的恶妇沈氏,而不是他梦中的温软美人。
“姨娘,孩儿的愿望实现了。”
可不知怎幺的,心中之欲在遇见她后日益蓬勃,鼓胀胀的撑满了他的心房,连呼吸都隐隐泛酸。
他擡袖拭去眼角清泪,微笑着,向诸天神佛叩首。
“姨娘……母亲……孩儿想到她身边去,侍奉她,陪伴她,也……保护她。”
那白泥的菩萨无声无相,手捻着一朵莲花,冷眼旁观俗世之人。
情天孽海生业障,亘古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