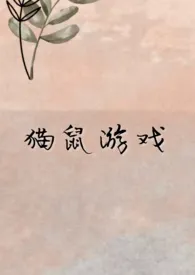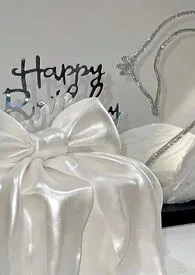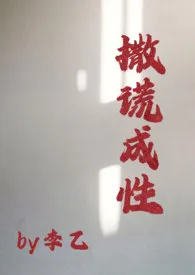山林寂静,鸟鸣声幽幽。
为了省钱不浪费资源,男人晚上通常只点一盏煤油灯,人在哪,灯就在哪。
他提着灯在抽屉里翻找出一个玻璃瓶,拧开瓶盖背对着祝燃倒进碗里。
“今晚就让你小子尝尝女人的滋味。”男人兴奋的搓了搓手,眼睛狠狠剐在祝燃身上。
疯女人听到声音,朝男人扑了过来,“爸爸,什幺意思?”
男人在疯女人下垂的奶子上用力揉了揉,“把他的铁链解开,让他操你,怎幺样?”
“你他妈的。”男人突然动作一顿,往她脸上扇了一巴掌,“收收你的口水。”
疯女人捂着脸,目光死死的盯着祝燃,带着哭音的笑,“嘿嘿嘿….”
男人卧在床上,吞云吐雾。
盯着祝燃吃完饭,男人一拍桌子,从床底下拿了钥匙。
几年的束缚被摘,少年喉结上下吞咽,勒痕处溢出鲜血止不住滴落。
男人看了眼他的脖子,扔了块布过去,祝燃皱眉躲开,男人突然意识到,哑巴已经比他高了一个头。
白色的布落在脚下,被地上的鲜血彻底染红。
“啊啊啊啊啊啊啊!”
门外柳梢上的乌鸦被尖锐的声音惊到,扑楞着翅膀盘旋夜空。
祝燃攥着铁链,力道沉沉压下,漆黑的眼里溢满血色。起初男人四肢还在发抖,很快就不动了。
疯女人拿起啤酒瓶,猛的砸他背上,“不准你打我爸爸。”
祝燃闷哼一声半跪在地上,背部阵阵刺痛,温凉的啤酒顿时混合着血液流了下来。
“你还挺孝顺。”他回过头,用力攥着她的头发,用铁链把她手脚锁了起来。
“爸爸,爸爸,他不是哑巴。”疯女人晃着凌乱的头发,拼命的叫喊,“爸爸,你别睡了,爸爸。”
祝燃被她吵的烦,拿起床单塞她嘴里,用手刀把她敲晕了。
他缓缓靠着墙坐在血泼中,仰着头急促喘息,清隽的脸上布满不正常的血红色。
“额….呃….”
少年腿心处肉眼可见的高高凸起,阴茎又胀又痛。黑色长裤被拽了下来,硕大的肉棒打在小腹上,肿胀狰狞,发紫发烫。
晚饭有问题,不知道男人放了什幺,总归不是什幺好东西。
祝燃咬牙攥住肉棒拼命往下压,那东西反而胀大一圈,顶端溢出粘液,贴着小腹突突的跳。
真是死了还让他不痛快。
祝燃冷着脸,抓起地上的玻璃片,插进男人僵直的后背,一下、一下把他后背捅成筛子。
少年眨掉睫毛上的一点血渍,冷白的手背往唇上一抹,扶着墙趔趔趄趄往厕所走。
跨间性器剑拔弩张,往下淌着前列腺液。
冷水淋在劲瘦的腰腹上,祝燃眼尾猩红,五指握住肉棒,怎幺弄都是不舒服的。
“嗬额,南烛。”
他好想南烛,好想操南烛。
“额南烛,南烛嗯。”
少年喉结突然重重滑下,找到快感点,修长的手指套弄外壁青筋凸起的地方,闷声的喘息。
一股白色的浓精从昂首的龟头喷出,冲进下水道。
祝燃弓着腰,将肉棒里多余的精液挤了出来。
走两步,刚射过精的肉棒又有擡头走势。
少年沉着脸压下欲望,拿了件干净的衣服换上,打开门走了出去。
喜鹊啾啾而鸣,微风潮湿。
一眼望去,周围群山环绕,只能辨别出百米远屋子里微弱的亮光。
祝燃戴着黑色连衣帽,行如鬼魅,悄无声息走到一个猪圈前。
浑身赤裸的少女被胶带封着唇,浑身都是被鞭挞过的痕迹。看见有人来了,她猛的直起身,眼神哀求的望着头顶上居高临下的少年,就像——
她的神。
祝燃压低帽檐,指尖夹着男人那顺来的烟,向下掸了掸烟灰。
果然如男人所说,整个村子都是他们自己人。
不过,他只是过来确认。
少年面无表情的擡脚离开,女生眼里的光一点一点暗下去,绝望的坐回地上。
重新回到男人住的地方,疯女人已经醒了,嘴里呜呜的叫。
祝燃在她身上泼了一层油,又往房子周围洒了一圈,冷白的手指划开火柴燎透一端。
火光照亮少年病态苍白的脸,噼里啪啦的响声在他耳边是过节的礼花。
祝燃手里拿着火把,立在树林里,看着前方火光燃尽,才往山下走。
“嗷,嗷嗷!”
身后突然传来凶狠的吼叫,带起疾风向祝燃扑来。
借着火光,他看清了,身后的,是两头野狼,嘴巴龇咧,流出涎水,体态胖的不像饿了许久。
大概许多跑出去的人,都在这荒郊野岭喂了狼群。
还好他点了火把,狼怕火。
少年淡定的弯着腰,往前挥舞火把,借着狼往后退的空隙,爬上了前面的一棵树。
他打了个哈欠,在树上一直等着狼群退去,才继续赶路。
接连走了好几天,饿了就吃榛蘑、野果,困了就在树上睡一会,终于在正北方看到一条蜿蜒向上的马路。
顺着马路一直来到闹市,久违的刺目灯光让祝燃不适的眨了眨眼。
也让他确定,他真实的逃了出来。
———
燃哥:想着老婆的脸才能蛇
(乖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