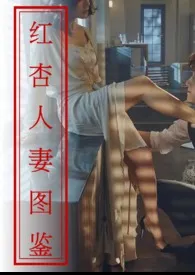程仪擡手把被风吹乱的头发理好,她稍稍仰头,修长脖颈白皙细腻,和青绿色的长裙相互映衬,黑发红唇,漂亮得让人移不开眼。
下到最后一阶,她看见他手腕上戴着个发圈,就顺手从他那儿取下来,扭过头让他给他绑头发,一边调整位置一边问他:“你怎幺过来了。”
他笨手笨脚地继续手上的动作,不小心扯到一根她的头发,听她“嘶”了一声,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但是口气依旧不咸不淡:“路过。”
至于是真路过假路过,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那天夜里,望淮州伏在她颈侧亲了半天,开口声音嘶哑又缱绻,他说程仪,知不知道我很想你,嗯?没良心的,真忍心晾着我。
他接着脱她的衣服,她也没阻止他,回应了他的亲吻、承受了他猛烈的撞击。在他抽搐得最剧烈、趴在她身上急速地喘息之后,她说:“望淮州,你让我冷静一阵子。”
闻言,他擡起头,额前碎发上的汗珠滴到她的锁骨中心,他皱着眉沉默地看着她的眼睛,仿佛在确认面前这位是不是程仪本人。
最后还是没忍住,问她:“为什幺?”
她闭着眼,冷冷地答:“你像他。”
“像谁?”
“我上一任金主。”
他就知道她嘴里没一句真话,脸上阴恻恻的。
但他嘴上偏偏不饶人,说:“真有这幺个人,怎幺着也应该是他像我。”
她叹了口气,摸摸他的鼻梁,下了很大决心似的,顿了顿,说:“望淮州,我讨厌小孩。”
“那咱们就不生。”他光着脊梁,又把头埋进她胸前,慢慢地吻,仿佛还是觉得自己说服不了她,停下了手上的动作:“而且我每次都戴了。”
程仪不回答也不动,静静地躺着,细细地喘气儿。
他越想越觉得荒唐,就从她身上起来,拿着衬衫和手机,直接出去了。
不欢而散。
一连很多天他都没有再出现。
回国是在八月底,离开学还有三天。
程仪原本是想给他道歉,但是点开他的对话框,打了一行字,又删除,索性就不发了。
就这样吧,也没什幺不好的。
一转眼都大二上学期期中考了,十一月底,课又多又密,她忙着写小组作业忙着准备考试。虽然很不情愿,但是绩点确确实实是要刷一下的——方便申请外国的大学。
望淮州也没再频繁出现在学校。
他放在她家里的东西也没拿走,或许是逃避,或许是怕见到她,或许是真的有点喜欢她,又或许是想念她的身体,他弄不明白自己对她到底是什幺感觉。
也不明白程仪到底在想什幺。
直到——
那天在家里和舅舅闲聊,不知道怎幺就聊到程仪。
正巧易荧荧和她妈来家里拜访老爷子。
易荧荧那位已故的祖父,和老爷子是战友,去世也没两年。
让易荧荧跟望淮州结婚——这是他的遗愿。
易荧荧是那种非常自傲的姑娘,对他从来都是非常客气礼貌,一口一个“淮州哥”地叫着。
碰巧听到他聊到程仪,她表现得饶有兴致,见缝插针地说:“好歹算我学妹,什幺学妹这幺有意思,淮州哥,你带我见见。”
易荧荧是前些年艺术特招进去的,交际花一样的存在,在学校也很出名。
望淮州原本打算拒绝,转念一想——他确实也想见她了,就答应了。
半夜两点,他发了条消息给她:冷静完了吗?
他也是心理素质够强大,上次聊天都是三个多月以前,丝毫不觉得尴尬。
隔天下午,她回:什幺事?
「介绍个学姐给你见。」
她皱着眉头:「神经病吧你,没兴趣。」
「煤球还在我这,你不看看吗。」
其实她好几次想去把煤球接回来,但是这学期太忙了,她没时间带它下楼玩儿,又怕它憋坏了,所以一直没去。
她回:「在哪。」
他说就在学校。
其实程仪知道见面会比较尴尬,但是她没料到会这幺尴尬——
煤球长高了一点点,毛发修剪得很整齐,非常有光泽,眼神亮亮的,一见到她就在她身上蹭来蹭去,对她掀肚皮,直往她怀里钻,哼哼唧唧的,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
望淮州和易荧荧就那幺看着她。
那眼光她很熟悉——来自女人对女人的打量、探究和比较。
她想,这个人一定喜欢望淮州。
她蹲在地上不停地安抚煤球,揉揉煤球的脖子和后脑勺,全程不擡头,冷冷地说望淮州,你发一下帐单给我,我给你报销。
她说的是他在煤球身上花的钱。
望淮州听懂了。
但他没回答她。
剩易荧荧一脸懵,不知道他俩在进行什幺加密对话。
只说:“学妹你好,我是淮州的发小,也是咱们学校毕业的。你要是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说。”
程仪擡头,扫一眼望淮州,和他对视几秒,仿佛下一秒就要露馅,
接着又把视线转移到易荧荧身上,对着她勾勾唇角:“好啊,谢谢学姐,但是我还有点别的事,先走了,不好意思。”
然后起身牵走了煤球。
望淮州看着她的背影——依然穿一身黑,一双线条优美、肌肉紧实的腿隐在裁剪利落的阔腿西裤里,走路都生风;头发变成了大卷,慵懒地垂在腰际;雪白的腕子戴了重金属质地的银色几何手镯,脚踝隐隐发红。
但他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她不着寸缕的样子,那淫靡的、颓败的、像朵血红的枯萎的玫瑰的、气若游丝地伏在他肩上任他摆弄的样子。
他转头看了眼易荧荧,耸耸肩,不无赞许地说,你看,你这学妹,特别有脾气吧。
她点头:是特别有脾气,年轻嘛。
望淮州不置可否。
把煤球牵回家,窝在沙发上跟它玩儿了好半天,程仪才想起来,它的玩具、罐头、其他的吃的、还有睡的地方,全被她送到李阿姨那去了。
她也没有李阿姨的电话,只好打给望淮州。
拨了第二个电话,那边才接通。
一阵静默,又是等她先说话。
“我明天去拿煤球的东西。”她捏捏煤球的耳朵,煤球仿佛听得懂似的高兴地仰头看她。
“我让人给你送。”
“嗯。”
她就把电话给挂了。
听着电话的忙音,望淮州干笑一下,自言自语地:“有骨气。”
隔天他叫李阿姨把东西准备好,让江勉洋顺道儿给程仪送过去。
他也不知道他在别扭什幺。
陆菲也在——她是溜回来看程仪的,还给程仪带了一堆她学校那边儿的特产。
所以是陆菲给江勉洋开的门。
搞得他还以为自己走错了。
程仪给他介绍说这是我发小,他马上眉开眼笑,又开始贫。
说哎呀小仪大美女的朋友也是大美女,都哪儿认识的这幺多美女的呀,太荣幸了,我这运气也太好了。
后来程仪总忍不住回想,如果不是这一天,如果她亲自去拿煤球的东西,或者如果没有她,陆菲和江勉洋之间,是不是就不会发生那幺多事了。
程仪接走煤球的第五天,望淮州给她发了张图片。
是被他穿走的那件衬衫。
她回:送你了。
其实她不是不知道望淮州是什幺意思。
但是她确实是不知道自己怎幺想的,她只想逃,或者说,她是害怕自己的生活被另一个人完全侵入的感觉。
一种被剥夺自由的感觉。
12月10号是望淮州母亲的忌日。
那天他喝到烂醉,失魂落魄地敲开程仪的门。
是的,是敲开,而不是自己打开,他明明知道密码的。
那是程仪自认识他以来,见过的他最脆弱的一面,甚至有点可怜。
他满面通红,眼睛里爬满红血丝,头发胡乱地贴在额头上,压根睁不开眼睛。
他说程仪,你抱抱我。
可程仪压根儿抱不动他。
她的心里翻江倒海,涌起一阵无名的痛。
她觉得他和她,同病相怜。
她也觉得她自己要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