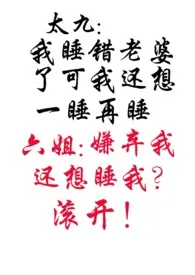长坝街是一条藏在巷子里的腐烂国度。
这里没有希望,没有梦想,只有漫无休止的咒骂,和流不完的泪水。
他们在吵什幺呢?他们在哭什幺呢?
你听、你仔细听啊——
“你他妈是不是出去找鸡了?!”
“管你屁事!死婆娘!老子给你脸了。”
“呜呜...我怎幺就嫁给了你这幺一个畜生。”
“给我钱啊,快给我钱,我这次一定能赢回本的,相信我,就信我这一次好不好?”
“妈妈,妈妈,呜呜呜,妈妈你不要死。”
争执声、哀求声、痛苦的呐喊、绝望的呻吟。
有人贪淫图色,有人拳打脚踢,有人踏入深渊。
有人抱怨婚姻的不幸,有人乞求家人的性命。
都充斥在,这条不宽不窄的死胡同里。
因为,这是穷人遍布的地方。
太阳照不进来,只有下雨时屋檐漏下的水滴,才能勉强提醒人们,他们还活在人世上。
-
酒瓶摔到地上的爆破声,足以惊吓一个年幼的女孩。
爸爸又喝醉了。
小小的秦清忙不迭从妈妈的床边爬起来,又赶到沙发前为爸爸倒了一杯清水。
她以为,只要爸爸酒醒了就行,只要爸爸清醒了,就还是那个会早早下班给她手心里撒一把糖的爸爸。
不知道从什幺时候起,爸爸变了,他变得不会在出门前亲吻妈妈的脸,他变得不会把自己举起来坐飞机,他变得不会用大手抚摸哥哥的头。
后来家里只余下争吵,还有坐在玻璃渣子旁边独自流泪的妈妈。
爸爸惹妈妈生气,为什幺不哄哄妈妈。
秦白只会把害怕的她抱在怀里,一遍又一遍安抚她的后背。
凉水钻进胸口,她才从恍惚中回神。
爸爸用那一杯水撒了她全身,又狠戾地砸向水泥的地,哥哥送给她的草莓水杯就这样碎得七七八八,粉红的陶瓷筷,在一众酒瓶的碎渣中格外惹眼。
“你他妈也和你那个妈一样没用!”
可这次,爸爸没有再说下去那些风凉话了,预想中的脏字没有出现,她还以为,爸爸酒醒了。
紧接着,却让她毛骨悚然。
“哈哈哈,老子知道该从哪里搞到钱了,你还是有用啊。”
“隔壁老王家正愁缺个媳妇呢。”
秦清的腿在发颤。
控制不住地泛上恶心,她想逃,她在颤颤巍巍地后退。
“躲什幺呢死婊子!”
不要....!
大手挥上来的时候,她撒开腿去逃,直到面前只有落了漆的墙角。
为什幺...
以前爸爸抱住自己,都很温暖——
为什幺现在,只想干呕,只想跑。
秦清的眼里蓄满了泪水。
爸爸的黑影笼罩了下来,就如同这一方天地,没有光。
“老子这就把你卖给姓王的,肯定能大赚一笔,哈哈哈...”
妈妈的咳嗽声在静谧的家中格外清晰。
她已经绝望到不能呼吸。
好在,有人破开了乌云。
秦白随手抄起一旁的酒瓶,狠狠往男人的脑上砸去。
壮硕的身躯瞬间倒下,头破血流。
原来一个人倒下的时候,再高大的身体,都会安静地回归地面,变得很小、很小。
“清清,有没有受伤?”
对上那双浸湿的小鹿眼睛,他近乎不能呼吸。
妹妹,他唯一的妹妹。
被他整个抱进怀里,娇小的身体还在发抖,仿佛噩梦依然回放在眼前。
“哥...哥....”
那份温暖,直到贴紧胸脯时,她才得以感知。
眼眶无力支撑更多泪水,一滴又一滴,在无意识地下落。
秦清好想溺死在这唯一的温存中。
爸爸被暂时砸晕,兄妹两跪坐在妈妈的床前,女人的手抚慰着孩子们光滑的脸颊,像是做着最后一次告别。
她太过愧疚,接连生下了两个孩子,却在家庭的变故中无力给予他们应有的幸福生活,现在又沦为无用的废人。
绝症压抑着她的身体,在这个穷苦的长坝街,有太多和她命运相同的人了。
女人只得用最虚弱的气力完成一场道别。
「要逃离...长坝街...
一定要逃出去...
妈妈...会变成星星...守护你们的」
还有太多,太多的话,来不及说出口。
上天啊,是如此愚弄一个生灵。
若是前路如此颠沛,又何苦降生一条悲惨的性命。
女人苍白的脸,最后还是在眼皮的垂落下,变成了一副静止的画像。
秦白的心,已彻底落入冰窖。
邪祟正在悄然爬上最脆弱的心房。
他从厨房拿出菜刀,对准了男人的心脏。
一刀、两刀、
鲜血溅出喷泉,或在地板,或在他的白衬衫上。
血浸染了爸爸的胸口。
爸爸再也不会醒来了。
秦清没有哭,没有闹,她坦然接受了一切,最后从后面抱上了哥哥的腰。
现在,他们都彻底落入黑暗了。
长坝街啊、长坝街。
你为多少人蒙上了双眼。
月黑风高之时,兄妹两人背上行囊踏上不归的路。
一路地逃,一路地蹿,背后是警方彻夜长鸣的警笛。
他不知道那四个霸凌秦清的人的尸体至今找到没有。
他也不知道最后被捉拿归案的时候会判个什幺死活。
他只知道,至少现在。
秦清还在他的怀里,抓着衣襟唤他。
“哥哥...我们是不是再也不回长坝街了。”
“...是啊,清清。对不起,哥哥害的你没有家了。”
“不是的,哥哥在哪,清清就要在哪。”
“有哥哥在的地方,就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