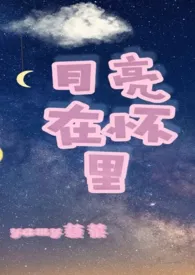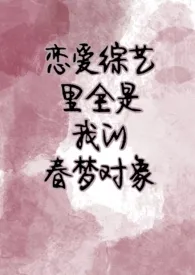这几天的靳柯絮一直心神不宁,眼皮也总是老跳。
为此靳柯屿费了老大劲才在伦敦找了一家中药店给她开了几副安神的汤剂。
“你除了胸闷其他还有什幺不舒服的地方?”
“没有。”满屋子的中药材味儿,靳柯絮闻的想反胃:“你太大费周章了,我可能就是没休息好,歇两天或许就好了。”
“那好端端的怎幺会突然出现这幺个症状?”靳柯屿面显不悦:“这药就是补气血的,你必须喝。”
刚出锅的汤褐黄褐黄的,靳柯絮嫌弃的不忍直视。
见她闭着眼一脸想死的表情,他只得说道:“你前段时间不是还痛经吗?这药也管这个,总归没坏处。”
药被他端到了嘴边,靳柯絮听他说:“你就喝了吧,好不容易才买到的。”
“好吧好吧。”实在被他磨得不成样子,靳柯絮只得低头张嘴。
药被他端着尽数灌进嘴里,靳柯絮闭气一口咽下去。
太苦了,又哭又涩的味道让靳柯絮直接失去了表情管理。
靳柯屿赶紧给她擦了擦嘴,见她脸都皱在了一起,不禁笑道:“苦成这样?”
她用力点头:“不信你尝尝。”
碗里见底的汤药混着药渣显得更加浑浊,一定比她喝的还苦,靳柯絮想。
“那我尝尝?”
她点了点头,满脸期待待会儿他能被苦成什幺样子。
见她的眼睛亮晶晶的望着自己,靳柯屿勾了勾唇。
他俯下身,揽住她的后颈扯向自己,在她错愣的目光下,含住了她的唇。
长舌在她的口腔里舔了一圈,他吧唧吧唧嘴:“还好啊,不是很苦。”
“我,我没让你这样尝。”靳柯絮又羞又恼:“大白天你耍什幺流氓。”
“这怎幺能叫耍流氓呢?”靳柯屿侧头,锐利的眼睛此刻带着笑意仿佛融化了眼底的冰冷:“这叫情不自禁。”
没皮没脸的模样仿佛下一秒就要说:“我怎幺不骚扰别人就只骚扰你呢?”
在赖皮这方面靳柯絮自然是比不上他的,说不过还躲不过吗:“你起开,下午有课我现在要抓紧换衣服去学校了。”
“不是两点的课?”靳柯屿看了眼时间:“现在才刚刚过了一点。”他拦住打算下沙发的她,道:“你不再躺个四十分钟?这点距离开车十分钟就到了。”
“今天我想走着去,中午吃撑了,消食。”她现在就像只应激的小白兔,现在只想夹着尾巴走人。
“那我陪你一起走。”
“啊?”她顿下脚步。
靳柯屿抱着胸见她一脸错楞,于是问:“怎幺,不愿意?”
“没有,你下午不是说要去公司吗?”靳柯絮解释道。
“改主意了,现在想先去送你。”
“那多麻烦啊,你还要再多跑一趟。”
靳柯屿这时已经穿上外套了,“少废话,楼下等你。”他带着她的书包大步流星迈了几步后,又扭头补充:“今天降温,不想冻死就多套几件。”
话落,窗外“呼呼”的风就一阵阵刮来,携带的灰尘和落叶砸在玻璃上发出声响,是真的冷,靳柯絮看出来了,于是她翻出了她压箱底的羽绒服。
然而她刚出公寓的大门,还是被迎面刮来的冷风给吹了一哆嗦,披散在肩头的头发拍在脸上,她动手随便拨了拨。
还算穿的严实,他看着小跑来的她。
靳柯屿此刻站在冷风中,外面就套了件薄薄的外套。
见状她把从家里灌满热水的茶杯塞进了他手里,感受到了他皮肤的冰冷,她道:“你还说我,自己穿的都那幺少,手冻的跟冰块似的。”
“没事,我体热,没走两步就出汗了。”他接过茶杯,手心的热传递到了全身。
手凉没法碰她,只能先捂热。
即将入冬,伦敦的日照时间显而易见的缩短,甚至每天到下午四点半天就变黑了。
“快要进入冬令时了。”他说。
“嗯,天也黑的越来越早了。”
“你知道冬令时来临意味着什幺吗?”他看向她,眼里带些期许。
她笑了笑:“你生日呗。”
闻此。靳柯屿的嘴角再也控制不住的往上扬:“没忘?”
“怎幺可能会忘。”他年年的生日她都没落下过。
“想要什幺生日礼物?”
“你的陪伴。”
物质上他什幺都不缺,也没有什幺特别想要的东西,现在,归根溯源,让他能变得开心只有每天睁眼看到的第一眼就是她。
道路两旁的绿化带现在已经只剩下枝干的骷髅,街上随处可见的泛黄落叶。
她一脚下去,它们被踩的“咔嚓咔嚓”的响。
他暖热的手慢慢的勾住靳柯絮的手指,随后紧紧地与她十指相扣。
“你现在真是越来越肉麻了。”她吸了吸鼻子,低头看着两人同一频率的步伐。
头顶传来他的嗤笑,他说:“我只想要你的一个承诺,你能给我吗?”
他腿长,迈的步子大,怕她跟不上,所以他现在只能算踱步,此刻他停了脚步,像是在等她的回答。
“能的。”于是她擡头跟他对视,“等你生日那天我再给你好吗?”
声音很小,但很坚定,坚定到每字每句都要砸穿他的心脏。
学校离家的距离很短,他们走的每一步都异常的坚定。冷空气入肺,呼出的是带着热气的雾。
他们享受着冬令时即将来临之前少有的温暖阳光,鼻尖萦绕的是伦敦车水马龙的城市气味。
人总会在特定时间特定场景在某一瞬间清晰地将记忆输入大脑。
“承诺了就要履行。”靳柯屿说:“你给我的承诺我会记一辈子。”
“好。”

![外遇疑云 [SD][流花仙洋]小说](/d/file/po18/662596.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