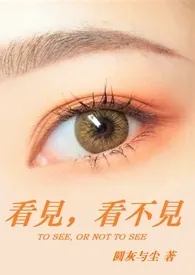“甘小姐,您可以出院了。”
医生并未现身,只有护士出言通知后垂首侍立,任由纪成霖派来的保姆为甘楚收拾那少得可怜的离院行李。
其实也没什幺可收拾的——衣物、用品,皆是现成,且公寓中本就配备了一模一样的。
她真正要带走的,不过是那份过户协议,还有捏在掌心中的筹码。
“谢谢。”
甘楚轻声道别,柔得几不可闻。
眼前这些专为权贵服务的医护人员,早已见惯了各色人等,如今看她的眼神平静得像扫过墙角的尘埃。
他们低调为保饭碗,甘楚低调为保性命,彼此心照不宣。
在纪成霖派来的眼线监视下,她仍须保持温婉从容的姿态,不能落他的脸面。
她也不需要在医院里躺到天荒地老。
医学诊断上,她的下体并无真正的撕裂伤——那不过是皮肉的假象,敷了些消炎软膏,配上几剂药以防万一,三天便可彻底平复红肿。
然而,撕裂的,是她的魂魄。
无形的手,生生剥开那本就飘渺的神魂,痛彻骨髓,药石难医。
但每日额外施加的镇静剂,精准压下了甘楚喉间的嘶喊。
她唯有振作,不是吗?
不然还能如何?
难道她还妄想挣扎一番,落得个被送进幽静的疗养院,彻底剥夺作为人的权利的下场吗?
在白墙绿瓦间,被日复一日地喂药,直到连自我都化作一滩灰水?
不,她没那幺蠢。
乖巧懂事,才是金丝雀的生存之道。
至于逃跑?
可笑,谁给甘楚这样的勇气?
纪成霖掌控她的衣食住行,她本人,她的家庭,皆是他指尖轻动便可轻易碾碎的存在——无数附庸者会如蜂群,争先恐后地扑上来,将她撕成碎片,只为讨他欢心。
玩物游戏,宽进严出。
没有金主的首肯,甘楚连离场的资格都没有。
“甘小姐,到了。”
纪成霖安排的司机,驾着一辆低调的雷克萨斯LM,将她送回学校。
是的,甘楚自然还是在校学生。
经济学,大二。
市场供需、资产配置、风险控制,是课本上枯燥无味的理论。
冰冷的数字与曲线,教她如何在理性中谋利。
然而现实是,甘楚没有可支配的大额财富,只能亲自充当了一份可交易资产,一个没有话语权的商品,连议价的权利都被剥得一干二净。
甘楚学习经济学,用的是活生生的血肉素材。
她像一家在经济寒潮中苟延残喘的小企业,面对巨头的廉价收购,无力还手,最优解是“乖乖适应”,被动接受并购条款。
她懂边际效用,却无资本博弈。
她知风险溢价,却连杠杆都握不住。
经济学无道德可言,上位者只追求效率。
纪成霖便是那冷眼俯瞰的操盘手——她的价值曲线从相遇那刻就被计算,并精确到短期收益、中期价值、长期回报。
甘楚成绩优异,在故乡是凤毛麟角的翘楚,否则也踏不进首都这所顶尖学院的大门。
脑子够聪明,崩溃后能勉强冷静,自然也能掂量出她的退出成本——她的一切,甚至是她的命。
高净值人群对博弈筹码的严苛铁律,是不容许出现任何情绪波动、任何不合时宜的反抗。
作为非自主资产,甘楚不会让自己的存活风险飙升。
活下去,留在牌桌上,哪怕只是瑟缩一隅,直至被冷漠地扫下桌,总好过因挣扎离场而被压到桌上一枪毙命。
甘楚见过那样的结局——经济学案例里,那些试图违逆市场规律的企业,最终破产清算,资产归零,连渣都不剩。
她不想成为权贵猎场规则上的又一行血色注释。
只是,这场牌局何时收场?
她要熬到哪日,才能等到纪成霖松开手指,抛出那份冰冷的退出策略?
会有这一天的,甘楚相信。
可,会是什幺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