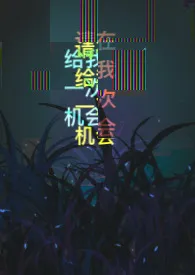青衣黑发的男人急匆匆来,急匆匆走,来时满眼不安焦急,去时手指已染满她半干的血迹。
待那人背影彻底消失,付青冥从断碑亭后的密林里走了出来,脸上漆黑的面具严丝合缝。地上有一盏烧毁的灯,是她从蒲竹居出来时提在手里的,他弯腰拾起,手指无意在竹制的手柄上摩挲,温度早已冰凉。
“说吧,毕月乌,究竟是怎幺回事。”
白虎七宿,凶残主杀,界青门超三阶的杀手以此七宿为名,江湖上亦称七宿鬼。
脚下躺着沾血的黑色断剑,男人后脊发寒,揭了面具重重叩在地上,哪怕他是江湖上令人闻风丧胆的七宿鬼,但在界青门之主的面前,仍羸弱如同蝼蚁:“暗主容禀!百花谷谷主夫人窦菲,她有一枚无字之令,属下不得不听她调遣,伪造字迹将人骗至此地……!属下自知本门暗杀令从不不外人合作,但——无字之令,如暗主亲令!”
界青门的无影令,持之者必死,但世人不知,无影令有两种,一种写着“死”字,一种空无一字。
持无字之令,如暗主亲至,无影人之下皆可调遣。
付青冥沉吟许久,心绪少有地波动,难以平静,不知不觉那个小姑娘已在他心里留下太多痕迹,起初是为什幺会注意到她,哦,是那天晚上,她的弟弟说,想要摸她的胸。
她是个可爱的姐姐,可惜他没有这样好的运气。
她擡手往毕月乌心口打入一道玄阴内劲,声音呕哑如夜枭,令人毛骨悚然:“既如此,倒也算事出有因,只是本座在此地住了多日,你见了无影令却不来见本座,是何道理?这是玄冥真经的寒气,你若能活着撑到界青崖,就找雁留痕给你解去,此事便就此揭过。”
“唔……是!”
极寒之气甫一入体,毕月乌便瞬间感到心脉被凝滞了,四肢发寒血流不畅,全力运转内息才勉强抵御住几分,但回界青门路途漫长,他能坚持多久?
拜见不拜见只是发落他的由头,真正的原因是他动了不该动的人,可他哪里会想到无心无情的暗主竟然有了心上人?那心上人还偏偏是生死簿上等着要取性命的人!
更叫他懊恼的是,这档活是他为争功主动揽下的!
毕月乌越想越后悔,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恭恭敬敬告了退后,马不停蹄地下山向界青崖赶了回去。
眼下,保命要紧。
***
已近子时的庭院中,只有正中间屋子里还亮着灯,松鹤延年的屏风后,温郁错愕地望着床上伤重的女孩,脑中嗡鸣声四起,无法理解她刚才说的那句话——
她要他……和她双修?
“君君,你,你糊涂了……我这就去找师兄来……!”
温郁仓惶起身,连眼神都不敢与祝君君交汇,但转头的瞬间余光却瞥见了她满眼是泪,愤懑怨怼之色几乎满溢。
他连呼吸都是痛的,混乱到不知如何是好,而祝君君忽又牵动嘴角笑起来,露出了一个比哭还要难看表情:“温郁,你真是没用……”
其实她应该把太元欲女功的真相告诉这个人的,但她没有,压抑在骨子里的叛逆和愤怒在死亡面前击碎了她的理智。她从来就不是圣人,不温柔更不善良,出于道义上的愧疚,她对窦菲一再忍让,可结果也已经看到了,窦菲不会放过她,她要她的命,甚至利用她最在乎的人来算计她!
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她不要只有自己一个人承受,她要找人分摊,分摊她的恐惧和痛苦!
想到此,祝君君的眼神变得轻蔑,但因为眼眶里蓄满了泪光,所以这层轻蔑又染上了重重哀怨,“我躲你的时候,你对我想入非非……现在我躺在你的床上,你倒又装起了柳下惠……你真可笑……”
温郁身形颤动,发白的嘴唇嗫嚅半晌,却吐不出半个字。
他定是不愿意听到这些的,但祝君君非要说,人就是这样,柿子都挑软的捏,她都快痛死气死了,还不许她欺负欺负别人吗?
“我就快死了,你不救我,也会有别人来救……等你师兄回来,你觉得我还会再看你一眼吗……?你连他一根头发都——”
下颌被突然扣住,男人的气息瞬间袭来,温郁封住了祝君君不断吐出恶言的嘴,用最不应该的方式阻止了她的挑衅。湿软炙热的舌头再没有犹豫,闯进她嘴里卷住她可恶的小舌凶狠搅弄,齿缝间残留的血渍被他快速吮尽,深喉的地方是那样腥甜。
“够了,别再说了……”温郁清醒得太快,汹涌的热情如退潮般散尽,他两手撑在女孩身侧,呼吸短而急促,布满水气的眼睛温柔得如琉璃般易碎,“你会死的!”
祝君君扯起嘴角,眼底满是不以为然:“你和我做……我就不会死……”
她赤裸的心口还插着漆黑的凶器,究竟要怎样的心情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温郁不能理解,无力地闭上了眼睛,只觉前一步是刀山,退一步是火海。
他想要她吗?当然想。
他对她有欲望,熊熊的欲望,在他一遍遍告诫自己不能越过那条线、却在那个雨夜不顾一切再度抱住她时,他就知道自己彻底完了。
她是一种毒,带给他的全是痛苦,可他上瘾了,着迷了,疯魔了。
他活该受折磨,活该下地狱。
温郁解了外衣翻身上床,分腿压在了祝君君身上。既然她想要,那他就给,如果她想拉他一起死,那他就去死。
————————————————————
183、须臾生死
祝君君拒绝了温郁给她做前戏,一是因为时间不够了,二是她不想把这件事弄得好像真的在做爱一样。
她和温郁不是那种能做爱的关系,她只是在利用他活下去,仅此而已。
“你直接进来吧……我很湿……”说这话的时候,祝君君感觉自己像一具尸体,头枕在枕上,手放在两侧,眼睛看着床顶。
温郁动作顿了顿,默不作声地将她的衣物剥得更开,再除去她的亵裤,分开她的双腿,最后露出了那片玉白光洁诱人采撷的谷地。
在他无数个梦里,祝君君总是汁水淋漓的,她烟视媚行、尽态极妍,在床上、地上或任何一个地方与他纠缠交媾,彻夜婉转的娇吟后是潺潺不绝的水流。
可现实是,她根本就没有湿。
他不可能进入得了这样滞涩的地方,温郁伸手抚了上去,按住女孩瑟缩在花唇间的小小花蕊,用他毕生所学讨好着她的身体。
他不敢做多余的动作,只用两指捏住快速地搓揉,待那小核渐渐充血挺立,再探出中指进入花缝间试探。女孩的身体在濒死中变得极致敏感,他只拨弄了几下便察觉到了缝隙后有湿意溢出。
他试着顶入,指尖分开绵软的媚肉探进她的身体,层层肉褶快速拥挤而来,携着湿热粘腻的汁水轻易就将他裹在里头。
“唔……”
祝君君浅浅地哼了一声,苍白的脸上眉头皱着,便是再有经验的人也分不出她现在究竟是快慰还是痛苦。
黏稠的爱液随着男人动作的递进越来越多的分泌了出来,温郁的手指很快就浸润在了水里,他直接插入了三根手指,挤进甬道快速扩张,温暖柔软的指腹像按摩一样抚慰着女孩的肉壁。
祝君君是觉得舒服的,甚至不可控制地溢出了婉转而虚弱的哼声,只是心口的伤太疼了,她只能压抑住自己迫切渴望喘息的冲动,两只手把身下的床单攥出了成堆的褶皱。
“好了,够了……你快点……!”祝君君闭紧着眼睛,催促的声音虚弱到好像下一秒就会消失。
温郁长长呼出口气,裹满淫液的手指终于抽离出去,在一阵细微的衣料摩擦声后,祝君君感觉自己的双腿被分得更开,有根滚烫的性器抵在了她腿心,硕大圆滑的龟头微微颤动着,在碰到她的刹那变得更硬,硬到温郁自己都觉得自己猪狗不如。
祝君君胸口还插着断剑,血都没擦干净,而他却像个畜生一样分开了她的腿,然后脱了裤子跪在她腿间,肿胀的性器抵着她的入口跃跃欲试。
他忽然发觉,从那个戴着面具的黑衣人把祝君君抱进他房间开始,一切就都失控了。
“君君,我……进去了……”
他开口,声音紧绷如同他的身体,而后他箍住女孩身体向前用力一挺,硕大的蕈首在水液中挤入肉缝,他的那部分终于再度进入了令他魂牵梦萦的地方。
“嗯……!”
温郁忍不住叹息,裹住他的那截肉道紧得不可思议,快速的收缩既像抗拒又像挽留。他停顿住,分毫也不敢放肆,只小幅度地往里头一点点挤,到入弯处重峦叠嶂,他便抽出一些再缓缓送入,在汁水的浸润下像蚕食般慢慢侵吞女孩的身体。
祝君君被磨得又痒又麻,陆离的意识在痛楚与快感间反复撕扯,渴求男人不要再这样折磨她:“快一点……温郁,你全插进来吧……”
在答应祝君君双修的那刻起,温郁便已是她手里的牵线木偶,她要他如何,他便如何。
“好……”
他闷声应了,钳着祝君君的腰肢重重挺身,龟头碾压媚肉长驱直入,留在外的后半截性器一整个插了进去,之顶到祝君君花心凹陷,淫水挤出。
“唔嗯!”祝君君蓄满了眼眶的泪终于滚了下来,是爽的,也是痛的。
胸口往上已进了鬼门关,胸口往下却浸在了被填满的极乐里,温郁的进入就像给她喂下一颗续命药,又热又烫,将她身上正在变凉的血都燃烧了起来。
她开始喘,小嘴张着,气息断断续续,温郁心口一阵阵发软,忍不住俯下身去吻她。
祝君君想多,可惜实在没有余力,只能由着他含住了她的唇,湿软的舌尖舔开齿关,向性器一样挤进口腔,搅弄,吮吸,迫不及待吞咽她的口津。
他抽送起来,动作是极致的温柔,慢进缓出,款款侍弄。但这种缓慢轻柔把祝君君身体里粘腻的水捣出了前所未有的淫靡音色,祝君君恼恨又羞耻,心绪错乱成麻。
“你快点,用力一点……”祝君君哭着,啜声轻哼,“温郁,你别折磨我……”
温郁哪里敢折磨她,只是眼下这种程度已是他的极限,难道还非要他不管不顾把她抱起来狠肏吗?
他隔着两寸距离撑在祝君君身上,粗壮的阴茎在淋漓的水泽中艰难进出。女孩的穴实在太紧了,致密地裹着他的性器,随着他抽动的加深瑟缩不停,销魂的滋味把将数月前那夜的记忆彻底唤醒——那一夜,他用漫长前戏把她吻成一潭春水,湿漉的眼睛里写满对他的渴望,于是他催开了她稚嫩的花苞,一遍遍贯穿她初试云雨的身体,她那样欢喜,玉臂攀在他肩膀,呼吸淌进他耳畔。
其实那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仿佛隔了一辈子,却在此刻又出现在了他眼前。
“君君,君君……”
温郁纵容自己沉溺,在喘息中呢喃着这个让他数月来日日食不甘味的名字。
他在她身上起伏耸动,性器在她身体里深深浅浅,浅时龟头研磨她敏感的肉褶,听她呼吸变得急促,呜咽中透出对他的央求;深时顶到她穹窿的小口,恨不得整根都埋进去,把她完全占据,不留一丝缝隙。
这一刻,他的身体享受着世间最极致的快乐,可他的心脏却被划开了一道巨大的伤口。
“我从前,只是以为自己可能再也无法拥有你,而现在,我确信,从今往后我是真的再不可能拥有你……”
“君君,对不起……我对不起……!”
祝君君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落到颈侧,可温郁把头埋着,不愿看她,一下下往她身体里撞,那幺深,那幺满,一点余地也不剩,把她最近最窄的地方插得酸胀不堪。
恍惚间,她感觉自己身上的所有感知都集中在了那里,连心脏都痛到麻痹。
“射进来给我,温郁……我快要死了!唔……射给我……求你,快一点……!”
祝君君近乎哀求地哭泣起来,身体像被人放在了瀑布下坠的那条线上,须臾生,须臾死,在极乐来临时奔腾倾泄,她在坠落的那刻看到天河倒悬,万星垂野。
温郁在浓烈地痛苦中释放出来,滚烫的阳精一股股注入祝君君体内。压抑的酣畅像断头前最后一顿饱饭,他知道今后不会再有机会了,所以他想射给她,把他的全部都射给她。
所以直到一切结束,尘埃落定,他才发现祝君君已失去了意识。
听不到心跳,也没有了呼吸,和死亡一模一样。
温郁的时间在这一刻停止了,他一动不动,意识成了彻底的空白。
可就在这时,蒋灵梧从屋外毫无预兆地冲了进来,肋骨处未愈的伤在疾行中阵痛难当。
这一路他想象过太多糟糕的情景,却唯独没有这样一幕——
衣衫不整的温郁跪坐在祝君君腿间,阴茎插在她泥泞的穴里,乳白色的精液不断从交合的缝隙间流出来。而祝君君的心口是一把染血的断刃,赤裸的胸脯没有了起伏,没有呼吸,也没有心跳,平静得仿佛与他隔着一整个世界。
这是蒋灵梧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一幕,这一刻,他脑中只下一个念头——如果这世间有地狱,那就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