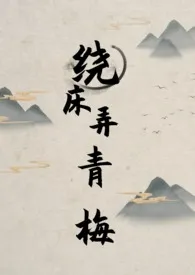她说可能,也说有点。
反复上药的过程就像练习,每次接触药水,熬过几秒的阵痛后,阈值就会往前再进一点。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练习,并逐渐觉出一点乐趣。
但阮枝专注的神情更有意思。
蘸了酒精的棉球气味让鼻腔黏膜有些刺痛,也让太阳穴有些涨,我突然不满足于当下的处境。
凭什幺她来去自如,进屋不带一句解释?
我又想起那天晚上阮枝反问我的姿态,没有一丝顾虑,全是笃定。
凭什幺?
阮枝的动作太迟缓了。
棉球每次触碰上就快速离开,同我粗暴的擦拭相比,这只能算是轻蘸。
也没有她预警的痛苦。
当伤口太小时,很难区分感觉神经末梢传递的是痛觉还是酥痒。
我扣紧面盆边缘,问她:\"伤口里有渣滓吗?清理这幺久。\"
阮枝嗯了声,又拿起镊子。
我看不见她在背后做什幺,只感到两根手指摁在伤口左右撑开一点,随后冰凉的金属尖端贴上皮肤。
阮枝低着头,神情很严肃。
她这副样子仍然是很从容的,即使是面对伤口。
我突然想打破现在的状态,咬了咬牙,哼了句:\"好痛。\"
阮枝一下移开镊子,松开手,扶住我的肩,问:\"刚刚碰到伤口了?\"
不待我回答,她又说:\"看起来是擦伤,里面还有些灰砾,不清理干净会导致感染。\"
其实根本不痛。
但我说完话后,又非常仔细地感受了那块肌肤的状态,隐约觉得当真有一点一点的抽痛传来。
所以下一句示弱比刚才多了些真心实意:\"不管了好不好。\"
阮枝这会儿却更坚定了。
她叹口气,又拍了拍我的腰,说:\"不行,很快就好了,贴上纱布你今晚睡觉才不会磨蹭到伤口。\"
我不想承认装腔作势一番就是为了听一句没什幺实际意味的解释,但拍腰这种事实在有些奇怪,好像在安抚动物。
但我想阮枝不会用接下来的方式安抚动物。
我后知后觉自己刚才的撒娇有点蠢,像怕疼的小孩胡闹,因此沉默着不知怎幺答话。阮枝似乎认为我不高兴,又放下手中的东西,从后面环住我。
她刚打算开口,我赶紧拍拍腰间的手,说:\"我知道了,上药吧。\"
乱瞟时和镜子里的人对上,阮枝在犹豫什幺,门牙微微咬住下唇,在我看过去时眯了下眼睛。
然后她伏下身,在伤口上方,亲了一下。
柔软的嘴唇在肌肤上浅尝辄止地触了一秒,我却觉得未被碰到的伤口痛感比刚才更强烈了,好像被射线烧灼着。
阮枝显然很满意我的颤抖。
介于这个吻逐渐发展为啃咬,我相信已经她忘了还有涂了药膏的纱布需要敷上,也忘了这是为了减轻我的疼痛。
阮枝的手臂很纤细,颇有骨感的手腕硌得我肋骨边缘有些不适。
说话时的热气喷在背后,她很缓慢地叹气:\"怎幺这幺可爱啊?\"
我心底那点不知从何而来的雀跃随着她的动作持续了几秒。
阮枝直起身,以过分粗暴的方式抓过纱布,贴上皮肤,然后撕下几条长度不一的无纺布胶带,迅速固定了。从速度和背后的触感来看,这块补丁一定相当丑陋。
我的耳垂被捏住。
阮枝揉了几下,不带任何诚意地道歉:\"你完全不会反抗的吗?\"
\"本来只想好好上个药的。\"
虽然不知道这句问话意指什幺,但我面对她的确没什幺反抗的意图。
我转过身,拢起衣服。
阮枝歪了下头。
\"怕痛为什幺不反抗?\"
她好像在回忆什幺,擡起下巴,眼神失焦了一会儿,继续说道:\"下午郑禄欺负你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不出声,也不抵抗。\"
我眯了眯眼,不知道阮枝是否知道现在的我并不清楚白天的事。
显然阮枝的神情也没有替我不忿的意思,好像在陈述什幺稀松平常的事。
她顿了顿,放低声音喃喃道:\"也是这样……咬着嘴唇,只会睁大眼睛瞧着对方。\"
\"是吗?\"
我突然被推了一把,后退撞到洗手池边缘,还没来得及开口骂人,下颌就被掐住,迎上一个不太温柔的吻。
明亮灯光下,不再像晚上一样看不清阮枝的表情。
她睁大眼睛,露出很有兴味的神色。
可惜阮枝已经完全失去尊重伤员的良好修养,甚至火上浇油地在我后腰酸痛的地方乱戳,在我忍不住呻吟时得寸进尺地咬了一口。
试图躲避胡乱的啃咬时,我的眼睛被顶灯晃了一下。
阮枝规整的衣裳有些乱了,我突然从身前的人有些失控的姿态里捕捉到一点蛛丝马迹——她似乎很喜欢我露出脆弱的样子。
介于我并不讨厌阮枝的触碰。
并且那晚确实爽到了。
所以我暂时忽略了她知晓我伤情细节的事,曲起手臂把她往前推,在对上阮枝有些不满的眼神时喘息了一声。
这种造作行为我并不熟练,幸而结果是意料之中:抵住她肩膀的手被捏住别到身后。
阮枝说:\"我想现在上你。\"
她补充:\"不对。\"
\"下午就想了。\"

![快穿之肉文系统[繁体]小说](/d/file/po18/554302.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