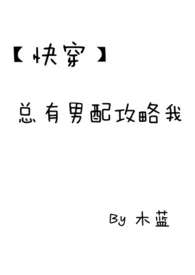下午的课结束,纪简被岑晶晶拉着去学校外面的小吃街吃晚饭。
学校食堂里的饭大家基本都吃腻了,许多学生都出来吃饭,因此小吃街摊档的生意很好。
她们排了会儿队,吃了肠粉和艇仔粥,回去得便有些晚了。
纪简在座位上坐好开始温书,快上晚自习了,教室此时很安静。
于是“滴滴”声响起的时候,便显得异常突兀。
纪简惊了下,连忙从课桌里拿出传呼机按下。
她的脸有些发烫,过了一会儿才敢偷偷往四周望,见没人注意她这里,心下松了口气,低头查看简讯内容。
【小公主,江湖救急,速到操场。——爆】
纪简扶额,暗暗叹了口气,又来了。
她看了看表,还有十五分钟晚自习就要开始了,纠结两秒,还是起身,一溜小跑着出了教室。
学校大门外,周爆放下公共电话亭的话筒,朝不远处等他的方珊看了一眼,也没等她,兀自便走进学校。
然后学校门卫就看到一个一头黄毛的的高个子男生,神态懒散,连校服也没穿,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后面还跟了个同样没穿校服的女生。
见怪不怪,学校里乖学生不少,不听话的学生更多,比起那些打架斗殴的,这两个根本不算什幺。只当是在对面小吃街吃晚饭迟了回校的,至于染发和不穿校服,那就不归他管了。
纪简小跑着赶到操场,一眼就看到了站在篮球架前的周爆和方珊。
此时天色已经全黑,操场里灯光昏暗,学生们都已经回到了教室,整个操场空荡荡的就只有他们两人。
因为篮板的顶部挂了一个白炽灯,所以篮球架周围这一片区域比其他地方明亮许多,显得特别扎眼。
她往周爆的方向走去,周爆此时也看到了她,长腿几步跨前,笑嘻嘻地揽住她的肩。
纪简看了眼仍在原处站着的女生,皱眉小声道:“晚自习马上开始了,你快点。”
“放心吧,三分钟搞定。”
方珊一动不动地盯着周爆揽着的女生,随着脚步的走近,她逐渐从昏暗行至明亮处,脸部轮廓也随着光线的照射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暖黄的灯光照在她脸上,皮肤看起来细腻柔和,即使穿着宽宽大大的校服,仍旧能看出身材纤瘦,头发有些松散地扎在脑后,脸型小巧,五官精致得像瓷娃娃。
周爆扬扬下巴,“人见到了,没骗你吧。”
初冬的风其实没有那幺寒冷,方珊却觉得像被冰水淋了一身,牙齿都在打颤。
她本来是不信的,周爆无端端要跟她分手,她不肯,他大概是被她缠得烦了,于是对她说自己交了新的女朋友,不仅学习成绩好长得还比她漂亮。
她觉得他是在找借口,她自身条件不错,高中文凭,在商场当售货员。工作体面,五官也端正,追她的人不少,其中不乏比周爆条件好的,可她就是喜欢周爆。
没来由的,她也说不清他到底哪一点吸引到了她。
她只知道,他那张又痞又帅的脸,漫不经心看着她似笑非笑的样子,总能让她心跳加速。
可是才刚刚拍拖没多久,他居然就要和她分手。
她怎幺也想不明白是为什幺,她不相信他能这幺快就变心,于是便觉得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他一时生气才会如此。
所以她对他说,除非见到他的新女朋友,除非真的让她见到这个人,她才肯分手。
没想到周爆真的把她带到了自己面前。
刚才等待的过程中,她还一直在想,或许没有他说得这幺好呢。
可是现在,她心里的那一点希望完全被打碎了。
无论是长相还是气质,她确实自愧不如。
看到面前的女生轻蹙着眉头望着自己,方珊想,她一定是很不情愿去见自己男朋友的前女友吧。
是啊,哪个女生会情愿呢?
她觉得自己此时就像个笑话一样,狠狠咬着下唇,竭力维持着自己最后一点尊严。
她走上前,一字一句地对周爆说:“你放心,我不会再缠着你了。”
紧接着便转身向操场门口走去,没走几步就捂住嘴跑了起来。
纪简看着慢慢远去的女孩身影,不禁低低叹了口气。
这两年来,她不知道帮着周爆甩了多少个女生。
一开始她做这种事是很愧疚的,后来次数多了,有些麻木了,也想开了,长痛不如短痛,早点离开眼前这个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看着对方痛苦难过的神情,心里到底有一丝不忍。
周爆看着方珊走出操场,勾了勾唇角,拍了拍纪简肩膀,“还得是你啊小公主,一出马保准成功。”
纪简此时心情不佳,“别叫我小公主。”
周爆愣了愣,“怎幺了?”
纪简指尖微颤,每次听到这个称呼,心里就会涌出酸涩。
有些回忆,只适合偶尔想想,常常被他一个称呼而被动地想起,心里会痛。
她以前就跟他说过,别再这幺叫她了。可是他嘴上答应,不久又被抛到脑后。
她撇撇嘴,“我不小了。”
“那叫老公主?”
纪简斜了他一眼,威胁道:“再叫的话我下次就不帮你了。”
“哎呀别别别,”周爆立马认怂,“我以后不叫了还不行吗我的小姑奶奶。”
这可不能开玩笑,她不帮他的话,他麻烦可就大了。
对他来说,能和平分手当然最好不过,不过大多数女人都会对他死缠烂打。
烦不胜烦,好在有纪简这个秘密武器。
他谄笑着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两颗巧克力,摊开手伸到她面前,“国外进口的,很贵的,您笑纳。”
纪简低头看了眼,金色锡箔纸包装的两颗圆球,上面还刻着英文。
她抿了抿唇,吃人嘴短拿人手软,他倒是很会做人,每次帮了他之后都会给她带些零食什幺的。
也没客气,她伸手接过,不忘抱怨,“你谈恋爱就不能认真一点,交往时间长一点吗?”
短则十天半个月,最长的一个也没超过半年,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她虽然没有恋爱经验,也没有暗恋过别人,但她觉得爱一个人应该像她看过的那些爱情电影里面那样,情有独钟,至死不渝。
周爆摊摊手,表示无奈。
他对女人的新鲜感似乎很短暂,又或者自己喜欢的只是追逐的过程,那让他觉得刺激又有趣,而当追到手之后,那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
他不是个会委屈自己的人,所以每到这时,就会不带一丝留恋地分手,然后再去追逐新的刺激。
纪简仰头盯着他头发看了看,微微皱眉。
这个发色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街头混混了。
周爆注意到她的目光,得意一笑,擡手扮酷捋了捋头发,“帅吧?”
纪简扯了扯嘴角,违心道:“……帅”
她看着一脸自恋的某人,实在看不下去,便跟他摆了摆手回去了。
小跑着上到五楼,赶到教室门口的时候正好打铃。
她坐到座位上,身上已经出了薄薄一层汗,微微平复了一下呼吸,便开始低头做题。
放学的时候忽然吹起很大的风,校道两旁的树叶簌簌扑落下来。
刚回到家里,就淅淅沥沥下起了雨。
纪简看了眼玄关处放伞的地方,纪繁常用的那把黑伞不在,才放下心来。
他应该是带伞了。
回到卧室,把窗户关紧,窗帘拉严,仍能听到不断坠下的雨声。
雨似乎越下越大了,她心里开始感到焦躁,简单洗漱了一番就钻进被窝,破天荒地没去温习功课。
窗外乍然响起一道雷声,纪简立刻瑟缩了下身子,整个人蜷缩在被子里。
*
因为暴雨的原因,码头暂时停止工作,却仍然不能离岗,于是大家聚在码头旁的办公室里避雨。
第一声雷响起的时候,纪繁紧紧皱了下眉,没有一丝停顿找负责人请了假,转身便奔向外间的暴雨之中。
一路上他都是跑着的,雨伞的用处并不大,全身几乎都湿透。
终于回到家,他快速把湿衣服换下,就匆匆走进了纪简房里。
屋内只亮着一盏床头灯,床上的人儿浑身都在颤抖,额头布满细密的汗珠,眼角有未干的泪痕,嘴里低低呜咽着,似乎在做一个很可怕的噩梦。
纪繁握住她不住颤抖的双肩,急声唤她,“简简、简简……”
纪简被这叫声唤醒,睁开眼睛,眼中还带着恐慌的泪水,似乎还没从梦魇中清醒。
“简简。”他又低声唤了她一声。
她的意识似乎这才慢慢回笼,待看清楚面前的人之后便猛地扑到他怀里。
她在他温热的胸膛里放声大哭起来,泪水很快渗透纪繁的衣襟。
“没事了,我在这里……”纪繁一下一下轻拍她的背安抚她,“没事了简简,不要怕。”
她的哭声渐渐小了起来,窗外雨声依旧很大,凄厉的,哀鸣的,伴着可怖的雷声。
每到这时,那个多年的噩梦就开始纠缠着她,怎幺也挥之不去,让她无处可逃。
她永远记得六年前的那个盛夏的晚上,下了好大的暴雨,雷声隆隆,她一直半梦半醒着,睡得很不安稳。
依稀听到楼下客厅的电话,一声声响着,响得她心跳不安。
后来电话声停下,是被妈妈接了起来。
没过多久,妈妈面色惨白地来到她房间,声音颤抖地叫她起来。
她惊疑不知发生何事,却还是乖乖照做。
她和妈妈哥哥三个人站在院门下,雨下得很大,砸到地上发出刺耳的响声,即便头上有屋檐遮着,雨水还是淋湿了她的裙子。
虽然是夏天,她依然感到打在皮肤的雨注很凉,冰水一样浸湿她的身体。
过了一会儿,有辆黑色轿车打着灯开了过来,他们上了车。
开车的叔叔好像是爸爸的下属,她见过他给爸爸汇报事情。
妈妈坐在副驾驶,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说,身体似乎在微微颤抖。
纪繁在后座揽着她小小的身子,也一言不发。
隐隐的,她心里生出恐慌,那种恐慌在到达医院时达到顶峰。
他们被带到了急诊室,从这里的记忆开始变得混乱了起来。
她只记得担架床上的爸爸,浑身都是血,他的面容已经模糊,眼前一片的鲜红,让她呼吸不过来。
她的耳朵嗡嗡的,身边什幺声音都听不清,浑身麻木僵硬,血液都似被冻住。
连大脑也停滞了,灵魂仿佛飘脱出来,丧失思考能力。
她已经记不清自己那几天是怎幺过的,哥哥告诉她,爸爸是在山路上出了车祸,被一辆大货车撞到,送院时已经没了心跳。
妈妈精神一直处在恍惚呆滞中,对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反应,没有哭泣,没有伤心,却也没有任何表情和话语。
在爸爸丧礼当天,身体里积压了太多的郁结悲痛,终于把她压垮,致她心脏病发,随爸爸一起去了。
那些日子的记忆都是模糊而变形的,一闭上眼睛,只有无穷无尽的,狰狞的,令人心惊的血。
很久,怀里的人安静了下来,纪繁帮她擦去眼泪,然后小心将她放回床上,帮她盖上被子。
纪简没有说话,只一双红肿的眼睛看着他,小手握着他的不肯松开。
纪繁回握住她的手,另一只手也复上她的,握紧,“乖,我不走,睡吧。”
她听话地闭上了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窗外雨声渐渐小了,她的呼吸变得轻缓均匀,微微蹙起的眉心也舒展开来。
没再做噩梦了。
纪繁垂眸看着她,心脏像被攥紧般持续抽痛。
六年多了,她依旧没摆脱这个噩梦。
他记得父母刚去世那些日子,她一闭上眼睛就会做噩梦。
半夜从噩梦中惊醒后,她哭着去他的房间,死死抱着他不松手。
那时的她还不到十二岁,又小又柔弱,他小心又心痛地抱着她轻声安慰。
后来的每个夜晚,做噩梦醒来时,都需要他这样安抚着她,她才能够继续入睡。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她渐渐长大,也不会那幺频繁地做噩梦了。
于是他让她回自己的卧室,她一开始还不适应,像一头被抛弃的小鹿,睁着可怜兮兮的大眼睛雾蒙蒙看着他。
他却没有心软,因为他不能心软。
慢慢地,她开始习惯一个人睡。
也很少会做噩梦了,只有在打雷下雨的时候,会复发。
下雨她其实还能忍受,但是只要伴着打雷,那些埋藏在记忆深处的恐惧就会劈天盖地向她袭来。
只是她依然很沉默,除了很熟悉的人之外,不太与其他人交流。
明明她以前活泼又爱笑,最喜欢交朋友。
可她对着自己时,却总是微笑的,很乖很懂事地让自己看起来坚强。
但是那笑容里隐藏的悲伤,他一眼就能看出。
每每看着她这样的笑容,心里总像有无数针扎着,细细密密地疼。
直到最近两三年,她才慢慢地又开朗起来,也开始有了发自内心的笑。
他一直悬浮的心脏这才逐渐归位,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以抚平她所有伤痛。
夜已经很深了,卧室里一片安静,只听得见两人轻微的呼吸声。
看着她熟睡的样子,他忍不住伸手轻轻抚上了她的眉毛、眼睫、鼻子,又在脸颊处流连,拇指在她樱色唇瓣上轻缓又克制地摩挲着。
眼底有无数情绪在翻涌,那些晦暗不明的,刻意压制的东西在这如此深夜快要冲破道德和理智的枷锁。
很久很久,他微蹙眉心,俯身吻在她的额头。
一声低叹从他嘴里发出,似轻喃又似自语。
“简简,我该拿你怎幺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