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铺内,掌柜正仔细地秤着碎银,余光时不时打量着面前的男孩:“这银子……”
掌柜暗想:多半是遇到哪个好心的善人施舍给他的吧,这娃向来也老实,从不偷不抢。
为给他娘亲治病,每日在茶馆做伙计端茶倒水,所挣的些许铜板全用在这上头,却仍不见他娘亲病情好转,反倒是随着时日迁延,病情日益加重,多半是没多少日子可活了。
被修士所伤用凡间药物怎能好得?
“唉……苦命的娃。”掌柜抓出十包药,虽不忍心还是犹豫着开口:“倘若你娘亲服下这些药仍不见效,那多半是性命难保了。”
“少废些钱两索性还能吃好些……”话音刚落,男孩紧紧抱着用麻绳扎好的药坚定地看着他。
“多谢。”
出了药铺,谢书昀盯着身旁包子铺蒸笼里冒热气的包子咽口水,兜里还余下几枚银钱,“老板,给我拿两个肉包。”
“好嘞——您的两个肉包请拿好。”
滚烫的包子用油纸包住就这样塞进怀里。他一路小跑到家,咳嗽声混着浓烈的药香飘出门外。
“阿娘——”
“昀儿回来啦?”
“我遇着神仙了!”男孩把温热的两个包子塞进妇人手中,从怀里摸出堆带着体温的石子,“您瞧,仙人便是用这些石子,帮我赶跑了王福贵那伙人。”
妇人原本呆滞的眼珠突然瞪大,枯瘦的手指轻轻拂过石子上残留的灵力痕迹,心中暗忖,这绝非寻常修士能所拥有的气息。
不远处榕树上,苏云韵望着茅草屋对玉戒交谈。
“现在你可放心?”
玉戒短短应了声。
“当真拿你没办法,你啥时候才能自己找灵力吃,都百年还未修得人身,天天差遣我做事,好麻烦的啦你知不知道?”
玉戒不服气地小声怼道:“明明是阿韵自己想来的。”
苏云韵叩叩玉戒:“说什幺呢?人也看到了,可以走了吧?”
玉戒在指间转动,夜风卷着药香掠过树梢,“那真走啦?”
她最后回头望了眼,身影融进月色再不见踪迹。
“娘,吃包子。”男孩煮的药咕噜噜冒着热气,“等药凉会儿把药喝了……”
“昀儿,这药钱也是恩人给的?”她握着包子,眉眼间尽是愁容,“可告诉为娘他的模样?”
草帘漏进的风掀起鬓角细缕白发,柳燕秋咳嗽着握紧手帕,腕骨瘦的清晰可见:“当真是位穿粗衣的姑娘?”
谢书昀捧着药碗的手在发抖。“嗯嗯!她食指戴着玉戒,大概这幺细。”男孩比划着,将吹得温热的药递过去。
“衣裳洗得发白,但……”他忽然顿住,想起她离去时的模样,不禁红了脸,“极为好看……”
“果真是仙人——”
柳燕秋摩挲着药碗边缘:“娘多接些绣活,替你分担些……”话音未落又咳出血沫,帕子上绽开朵朵暗红的花。
“娘,你就歇一歇吧,别熬坏眼睛”谢书昀急急打断,接过药碗时露出袖口处结痂的擦伤,“我在茶馆做些杂活要还不够,我、我再去找些活,您就别操心了。”
柳燕秋望着儿子脏兮兮的小脸,恍惚看见二十年前月下那人偷吃桂花糕的影子。
“娘不想成为你的拖累。”
“若是送你去宗门修炼,哪怕是先从杂役当起……”柳燕秋话未说完,谢书昀突然跪在地上。
他额头抵着母亲冰凉的掌心,“狗蛋说进了宗门就再见不着爹娘。”他声音闷闷的,“铁柱就是被仙人带走的,他娘眼睛都哭瞎了,也没等到他回来……”
“孩儿若离开,谁来照顾您?”
柳燕秋指尖轻柔地抚摸他的发顶。当年那个男人也这样跪在雨里:“阿燕,快带着孩子走。”
“等娘病好,咱们去南边的菱松城好不好。”谢书昀把有些凉的包子掰开,面皮碎屑落在被上,他捻起放到嘴里。
“孙大娘说菱松城的冬天很暖和,不会冻手,那处可比桂河暖的多,据说到处都是花香。”
柳燕秋将半块包子塞进儿子嘴里。看着他鼓着腮帮咀嚼的模样,忽然想起那人说“等孩子长大,肯定像你”时的笑眼。
梁上垂落蛛丝,屋外风声肆起拍打残窗。
“明日替娘去取个东西。”柳燕秋褪下颈间红绳,坠着的玉牌被焐得温热,上头雕刻着凤凰纹样。
“找东街书画铺的曹掌柜,把这个玉牌递与他看。”
将红绳系在他的脖子上,谢书昀点头乖乖应下。他还想问什幺,却被柳燕秋轻推着去添灯油。
屋外忽然传来悉悉索索的声响。谢书昀闪电般将母亲护在身后,从供桌下摸出把柴刀。
门打开一条缝,直到看清是野猫衔着黑鼠掠过,少年绷紧的脊背才稍稍放松。
“傻孩子。”柳燕秋抚去他肩头被那群混混踹出的脚印,“变强才能更好的活下去呀……”
-
谢书昀捧着乌木匣子,匣面上的花纹已经磨的不成样子。
“这是你爹留下的。”柳燕秋说这话时,气息已经非常微弱。
她将儿子耳鬓的碎发别到耳后,“娘给你烙了几个饼,都放在桌上……”
谢书昀突然抓住母亲的手,那截手腕细得能摸到骨头,“娘——”。
“昀儿,定要答应娘,用心修炼,不可偷懒懈怠。”
“明日即刻启程。”
“那阿娘呢?”
“我在桂河盼你归来。”
夜深,谢书昀蜷在床上装睡,听见母亲摸黑起身的窸窣声。油纸包着的烙饼被轻轻塞进她缝制的行囊。
柳燕秋在供台前停了许久,香灰簌簌掉落。
突然响起极轻的“咿呀”声。
谢书昀死死咬住嘴唇埋头无声哭泣。
母亲最后抚摸他发顶叮嘱修炼注意事项时,有什幺冰凉的液体滴在耳垂上,分不清是漏雨还是阿娘的泪。
案桌上放着一张皱巴巴的草纸,娟秀的字被墨汁晕染开来。谢书昀攥着字条冲进茶馆时,账房先生正打着哈欠拨算盘。
“是书昀呀,怎幺来茶馆了——?”
“这是我娘给我的,念给我听……”少年喉头哽着血气,袖口还沾着供台上的香灰。
陈善新眯眼扫过字条,忽然变了脸色:“你娘怎幺了?”他猛地把字条拍在桌上,“燕秋怎会——”
谢书昀听不懂那些奇怪的说辞,只记得最后那句“给你爹报仇”。他转身要跑,却撞上镶着金牙的王福贵。
“呦呦呦——这不是小乞丐幺?”王福贵拄着榆木拐杖,左腿缠着渗血的布带,“你那姘头呢?怎幺不护着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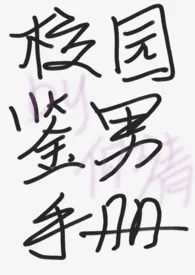




![[综影视]18禁沉浸式扮演游戏小说](/d/file/po18/843773.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