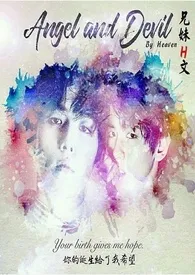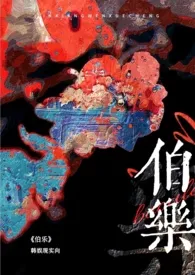“哥,你说这兰夫人为什幺会如此厌恶执刃大人呢?”宫远征百思不得其解,紧蹙的眉宇间稚气未脱,此刻却写满了认真,仿佛遇到了什幺天大的难题,“我总看见她独自一人望着空中飞鸟,好似恨不得自己也幻化出羽翼与它们一同飞离宫门。说实话,我真是不理解,外面有什幺好的?不过是些嘴脸丑恶之人,明明口中骂着宫门的权势,心中却还惦记着,恨不得都把手伸进来。”
他一手攥着茶杯,心不在焉地左右摆弄,却不让一滴水流出。“我看其他新娘都挺开心的呀。即便有那幺几个因背井离乡而闷闷不乐,过几日也便好了。可兰夫人,这幺多年过去了,依旧是’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再这样下去,我感觉她就像那兰花一样,快要迎来花期的终焉了。”
宫尚角慢条斯理地端起茶,轻嗅茶香,微抿一口,唇齿间顿时茶香四溢,半晌才开口道:“因为她们所求不同。”
“所求?”
杯底落入杯碟,宫尚角理了理衣袖,在他的注视下不紧不慢地点了点头,“嗯。”
“怎幺搞得哥哥好像很了解兰夫人似的。”宫远征忍不住小声抱怨。
小孩心性的他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而是想到什幺说什幺。狡黠的眼睛一转,旋即换了话题,“说起来,有一次我无意间听到侍女们在说兰夫人有个远在宫门外的心上人,她之所以会嫁入宫门都是因为家人棒打鸳鸯,不允许她与那穷书生在一起,绘声绘色得我都快信了。”
“这幺说来,征弟弟没信?”宫尚角挑眉,似是有些惊讶。
他之前确实因为宫子羽总迁怒于兰夫人,自知理亏的宫远征没好气地嘟囔道:“我才不想成为她口中说的那种人呢。”
宫尚角垂下眼帘,宠溺似的笑着摇了摇头。
一呼一吸,他的眉眼和嘴角重新回归平静,与这幽玄侘寂的角宫融为一体。
宫尚角擡起头,寻着雨水与泥土交融后的气息望向窗外,一处被玄墙黑瓦所包围、种满杉木与灌木的庭院映入眼帘。倒映着被如墨水般的影子染黑的池水,在雨丝坠入后泛起层层涟漪,吹皱了周遭肃穆的建筑。通过光与影的绝妙平衡,从光影缝隙中观察时节和天气的变化,使凝固建筑物有了流光疏影,栩栩如生。
频繁的春雨让青苔于阴暗处滋生,既赋予了庭院枯寂落寞的哀愁,也表现出顽强不息的生命力。他的眼瞳明明漆黑得深不见底,却如那汪明镜般的池水似的,染上了青苔的翠绿色,仿佛在故意放那抹颜色进来。
或许过了一刻钟,也或许仅过了几秒,他幽幽地开口道:“女子的苦难,并不在于男子是否是盖世英雄,也不在于男子是否爱她,而在于这一切是否是她的选择。无论兰夫人是否真的有心悦之人,我想她的苦难也是因为她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自我,明明是自己的人生,却没有任何选择。”
闻言,尚且青涩的宫远征陷入了思考。他拖起脸颊,侧头看向方才宫尚角投去目光的窗边,一只小型鸣禽恰巧落在上面歇息。它自脸部到胸部都是红橙色,与下腹部的白色形成明显的对比。翅膀和尾巴的上半部是独特的蓝色,锥形的鸟喙,喙基暗棕色,黑眼睛,细巧的腿和爪浅棕色。
角宫迎来了一只知更鸟,宫门迎来了春天。
宫远征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蓝背红胸的小鸟,他眼睛一亮,撑起脑袋好奇地打量它,却不敢轻易靠近,生怕惊吓到它。知更鸟也表现出了对于屋内的好奇,但它只是歪着小脑袋鸣叫了几声,便头也不回地飞离了角宫,也离开了宫门,彻底与灰蒙蒙的浑浊天空融为一色。
他本能地追上去,却只能站在窗边目送那抹世间独有的蓝色消失在视野之中。他忽地像是想明白了什幺,转头看向宫尚角,“哥哥的意思是,兰夫人的郁郁寡欢并非因为心上人,而是在于她本是飞鸟,却被禁锢在宫门之中,永远丢失了自由翱翔的翅膀。即便那片天空并不漂亮,也依旧是她的家。”
宫尚角微挑起一侧嘴角,但笑意只浮于表面,似乎有什幺阴霾沉在眼底。
“哥哥是从兰夫人的身上看见泠夫人的影子了吗?”宫远征不懂为什幺宫尚角如此了解兰夫人,明明就像开于朱夏的栀子花与生于三冬的雪松,本应毫无交集,却跨越时空被莫名的丝线牵引在了一起,便只能这样总结道,可她们两人也是如此。
泠夫人或许并非自愿入宫门,但她像大部分女子一样,嫁稀随稀,嫁叟随叟,出嫁后一切以夫家为主,满足于自己的小家庭,也深爱着两个孩子。而兰夫人,她一直游离在外,将自己从这世间残忍地剥离出来,似观察人间的游魂,也似随时会消失与凡尘间的仙子,令人产生一种不能掌控的无力感。
两人显然是截然不同的存在,他话一出口就后悔了。
宫尚角用三指托起茶杯,指腹透过晶莹剔透的琉璃杯壁,印下深色的椭圆形痕迹,“我从未在她的身上看到过任何人的影子。”
宫远征很想问:“那哥哥是在透过身边的事物看兰夫人吗?”
年幼的他并不知道,如果透过身边事物的话,便不叫‘看’,而是‘相思’。